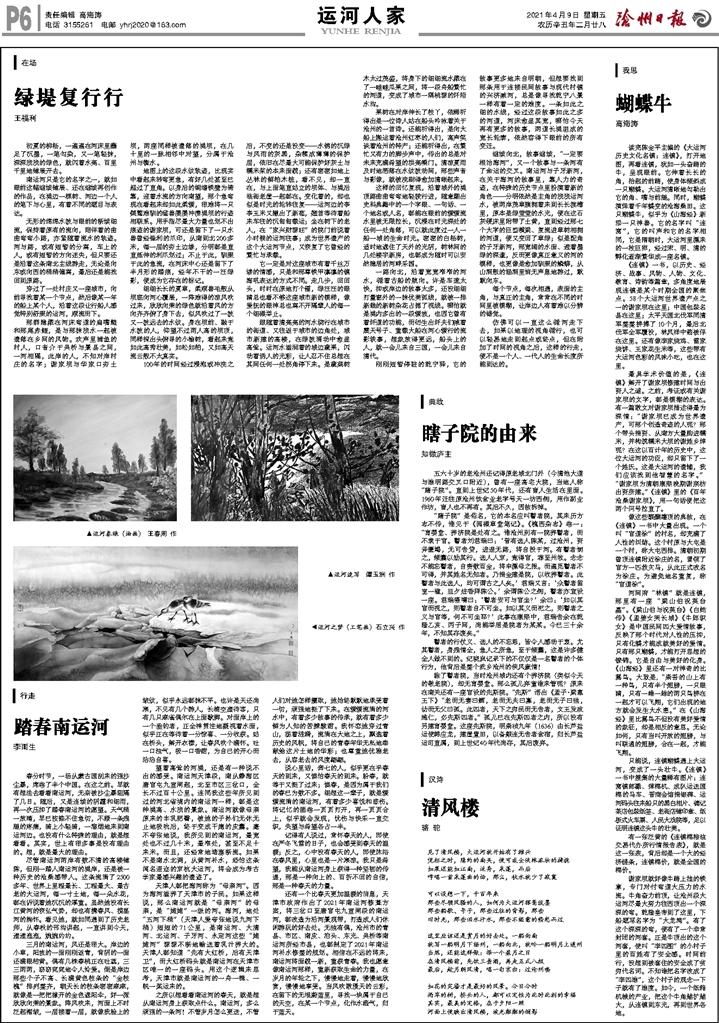五六十岁的老沧州还记得原老城北门外(今清池大道与维明路交叉口附近),曾有一座高宅大院,当地人称“瞎子院”。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盲人生活在里面。1960年迁往原沧州饮食业老字号天一坊西侧,用作副业作坊,盲人也不再有。其后不久,因故拆掉。
“瞎子院”是俗名,它的本名应叫瞽者院,其来历方志不传,惟见于《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一:“育婴堂、养济院是处有之。惟沧州别有一院养瞽者,而不隶于官。瞽者刘君瑞曰:‘昔有选人陈某,过沧州,资斧匮竭,无可告贷,进退无路,将自投于河。有瞽者悯之,倾囊以助其行。选人入京,竟得官,荐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赍数百金,将申漂母之报。而遍觅瞽者不可得,并其姓名无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养瞽者。此瞽者与此选人,均可谓古之人矣。’君瑞又言:‘众瞽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陈公。’余谓陈公之侧,瞽者亦宜设一座。君瑞嗫嚅曰:‘瞽者安可与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视之,则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义而祀之,则瞽者之义与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间,尚能举居是院者为某某。今已三十余年,不知其存废矣。”
瞽者的行仗义、选人的不忘恩,皆令人感动于衷。尤其瞽者,身残情全,急人之所急,至于倾囊,这是许多健全人做不到的。纪晓岚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名瞽者的个体行为,他背后是整个武乡沧州的侠风豪情!
除了瞽者院,当时沧州城内还有个养济院(类似今天的敬老院),却无育婴堂。那么孤儿弃童谁来管呢?原来在南关还有一座官设的先斯院。“先斯”语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孤儿已在先斯四者之内,所以没有另建育婴堂。这座先斯院,明崇祯九年(1636)由长芦盐运使韩应龙,建屋置田,以备颠连无告者食宿,归长芦盐运司直属,到上世纪40年代尚存,其后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