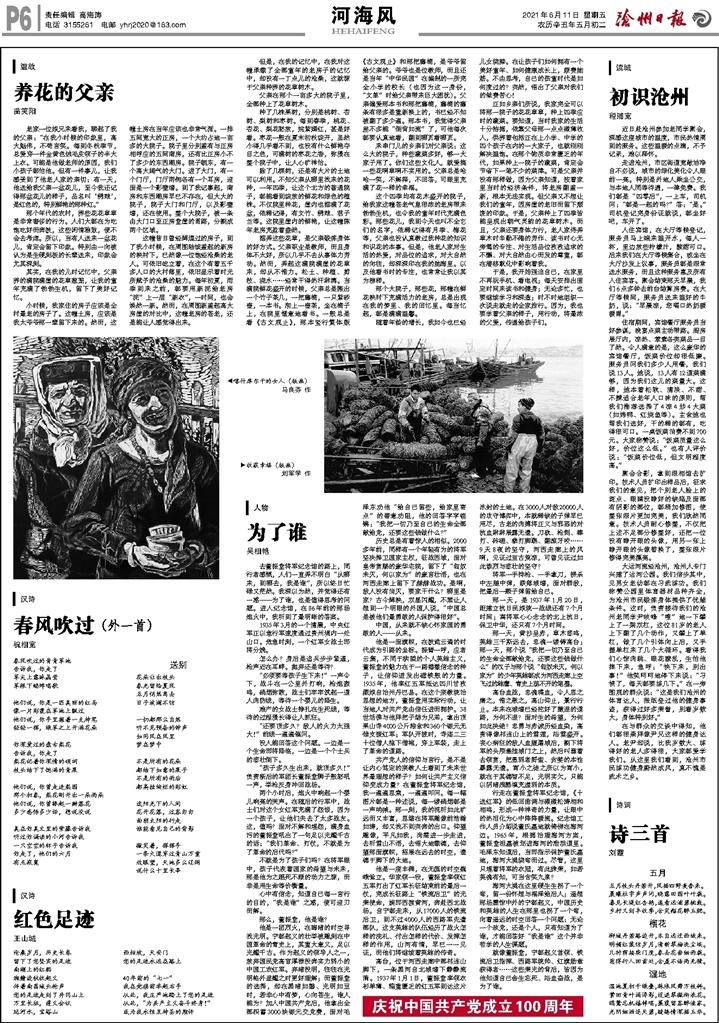去董振堂将军纪念馆的路上,同行者感慨,人们一直弄不明白“从哪来,到哪去,我是谁”,所以终日忙碌又茫然。我深以为然,并觉得还有一惑——为了谁,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进入纪念馆,在86年前的那场炮火中,我听到了最明晰的答案。
1935年3月的一个清晨,中央红军正以急行军速度通过贵州境内一处山口。危急时刻,一个红军女战士即将分娩。
怎么办?身后是追兵步步紧逼,枪声近在耳畔。抛弃还是等待?
“必须要等孩子生下来!”一声令下,战斗在一公里外打响,枪炮轰鸣,硝烟弥散,战士们牢牢筑起一道人肉防线,等待一个婴儿的降生。
难产的女战士挣扎在生死线,等待的过程漫长得让人抓狂。
“还要顶多久?敌人的火力太强大!”前线一遍遍催问。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一边是一个生命即将降临,一边是一个个士兵的悲壮倒下。
“孩子多久生出来,就顶多久!”负责断后的军团长董振堂狮子般怒吼一声,举枪反身冲回战场。
两个小时后,炮火中响起一个婴儿响亮的哭声。在随后的行军中,战士们对这个女红军充满了怨恨,因为一个孩子,让他们失去了太多战友。这,值吗?面对不解和埋怨,满身血污的董振堂吼出了一句足以光耀千古的话:“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革命的后代吗?”
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在将军眼中,孩子代表着国家的希望与未来,那是他为之蹈死不顾的动力之源,而非是用生命等价衡量。
心中有信念,知道自己每一言行的目的,“我是谁”之惑,便可迎刃而解。
那么,董振堂,他是谁?
他是一团烈火,在晦暗的时空寻找光明。宁都起义的壮举被雕刻在中国革命的青史上,其重大意义,足以光耀千古。作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放弃国民党高官厚禄投奔实力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弃暗投明,往往在光明格外显耀之时更好理解;而董振堂的选择,却在黑暗如磐、光明如豆时,若非心中有梦,心向苍生,谁人能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拿出全部积蓄3000块银元交党费,面对毛泽东劝他“给自己留些,给家里寄点”的善意劝阻,他的回答字字铿锵:“我把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党,还要这些钱做什么?”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2000多年前,同样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征战西域,面对皇帝赏赐的豪华宅院,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也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赫赫战功。是啊,敌人没有消灭,要家干什么?哪里是家?古今辉映,双星闪耀,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明眼的外国人说,“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中国,从来就不缺心怀家国的勇敢的人——从来。
他是一面旗帜,在波诡云谲的时代成为引路的坐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同于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董振堂的魅力在于一路播撒信念的种子,让信仰迸发出磁铁般的力量。1935年,他率红五军抵达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在这个宗教统治思想的地方,董振堂用实际行动,让当地人对共产党由信任进而拥护。38世活佛与他拜把子结为兄弟,拿出顶果山寺4000公斤粮食和360个银元无偿支援红军;军队开拔时,寺庙二三十位僧人拖下僧袍,穿上军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人的信仰与言行,是不是让内心笃定的宗教人士看到了未来世界最理想的样子?如何让共产主义信仰变成力量?在董振堂将军纪念馆,我一遍遍思索,一遍遍叩问。每一幅图片都是一种述说,每一缕硝烟都是一声呐喊。那一刻,我的视听如此旷远而又丰富,思绪在将军雕像前浩瀚如涛,却又找不到突奔的出口。仰望雕像,平凡如我,尚需进一步走进,去听雪山不语,去悟大地载德,去仰望那面旗帜,招展在远去的时空,遗德于脚下的大地。
他是一座丰碑,在无涯的时空巍峨耸立。华家领一役,董振堂率领红五军打出了红军长征结束前的最后一仗,完成长征路上“铁流后卫”的光荣使命,旋即西渡黄河,奔赴西北战场。自宁都走来,从17000人的铁流后卫,到不过4000人的西路军先遣部队,这支英雄的队伍经历了战火怎样的洗礼、付出怎样的代价、发挥怎样的作用,山河有情,早已一一见证,而他们将继续着英雄的传奇。
高台,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脚下,一条黑河自北城墙下静静流淌。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领衣衫单薄、辎重匮乏的红五军到达这片冰封的土地。在3000人对敌20000人的攻守博弈中,本就稀缺的子弹早已用尽,古老的肉搏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血淋淋展露无遗。刀砍、枪刺、棒打、砖砸、拳打脚踢、翻滚牙咬……9天8夜的坚守,河西走廊上的风啊,见证过亘古荒凉,可曾见证过如此惨烈与悲壮的坚守?
将军一手持枪、一手拿刀,拼杀中左腿中弹,跌落城墙,面对群敌,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那一天,是1937年1月20日,距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7个月时间;离将军心心念念的北上抗日,保卫中华,还只有7个月时间。
那一天,黄沙呈赤,草木悲鸣,英雄三千斯远去,忠魂一缕铸高台;那一天,那个说“我把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党,还要这些钱做什么”的汉子与那个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少年英雄都成为河西走廊上空飞过的雄鹰、青史上荡不开的笔墨。
高台血战,忠魂喋血,令人思之痛之,惜之敬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本来在城墙已经挖好了撤退的道路,为何不退?面对生的希望,为何如此决绝?忠勇与赤诚历经血染,高贵得像祁连山上的雪莲,浴雪盛开。丧心病狂的敌人血腥屠城后,割下将军的头颅悬挂城门之上,然后叫嚣着去领赏,把愚弱者野蛮、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宵小之徒之所以为宵小,就在于其德智不足,光明实欠,只能以阴暗残酷填充虚弱的本质。
行走在董振堂将军纪念馆,《十送红军》的低回曲调与微微松涛相和相鸣,形成一种神奇的力量,让眼中的热泪化为心中阵阵暖流。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说董氏墓地就倚傍在海河边。1965年,根据治理海河方案,董振堂祖墓被划进海河的泄洪道里。毛泽东知道后,当即指示保护董氏墓地,海河大堤绕弯而过。尽管,这里只埋着将军的衣冠,有此殊荣,如若英魂有知,可当含笑九泉?
海河大堤在这里硬生生拐了一个弯,留一份怀想与福泽给后人;遥想那场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中国历史和英雄的人生在那里也拐了一个弯,向着遥远的时空回答一个问题:无论一个政党,还是个人,只有知道为了谁,才能回答好“我是谁”这个并非哲学的人生课题。
就像董振堂,宁都起义首领、铁流后卫指挥、西路军统帅、红旗勋章获得者……这些荣光的背后,皆因为他知道自己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是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