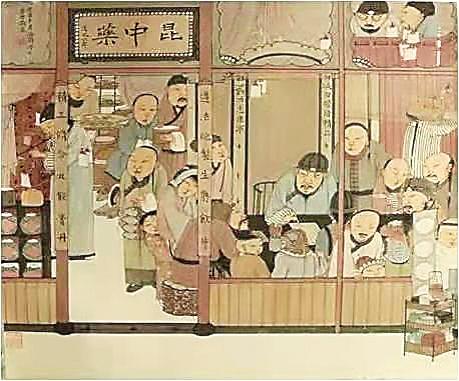石膏是一味中药,在张锡纯那里被运用得出神入化,多有起死回生之功,他因此被世人誉为“石膏先生”。
重识生石膏
巧救士兵命
张锡纯的长子7岁时患风寒,四五天之内,舌苔黄而带黑,身上大热。虽然张锡纯精通医术,但孩子小不愿意服药,逼着服药,很快又会呕吐不止,闹得这位名医也没了办法。
看此时的症候,应用生石膏,但生石膏大寒,小孩用行吗?此时,张锡纯对生石膏还不太了解,犯了嘀咕。思来想去,张锡纯想起中医里一句名言:“有是证则用是药”,意思是只要有症候,就应使用对证的药,即使药威猛霸道。于是他就用生石膏1两煎汤,趁着温热,给孩子分三次慢慢服下。让人高兴的是,病情开始好转。于是,增加到2两熬汤,慢服,病情继续好转。这回,张锡纯胆子就大了,他再用生石膏3两熬汤,给孩子服下。想不到,病好了!
一天之内用生石膏6两,孩子受寒了吗?张锡纯体会,病好以后孩子的饮食有加,没有受寒之象。他不免产生生石膏是大寒之药的疑惑。再翻看《神农本草经》,里面说石膏“微寒”,他不禁恍然大悟,此前自己未确知石膏之性。
张锡纯最有心得的一味药是生石膏,他记载最多的也是它。对生石膏的药性,他是从儿子身上获得的。后来张锡纯感慨地说:生石膏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
1916年年初,张锡纯随所在巡防营调动,从广平移师德州。他们在邯郸上车,向北进发。正月天寒,冷风从破车窗吹入,寒彻骨髓,到德州时,同行的五六个人都病了。发烧,但无汗。这就是伤寒。如不控制,则会入里化热,发烧、心烦,伴有出汗的症状。如果出汗,当用白虎汤,如果不出汗,说明体表仍为寒邪所闭,用麻杏石甘汤等。
这是张仲景留下的方子,但张锡纯没拘泥于原方。他见这些士兵都不出汗,身上发热,就用生石膏二两合半两粳米碾成细末,用水3碗熬,等米熟汤好,趁热喝汤汁,借汤汁的热气发汗。巧妙的是,热汤发汗,生石膏能祛除内里的热邪,粳米能防止生石膏伤胃,可使生石膏的药性留于胃中,长时间发挥作用。士兵喝完热汤出了一身汗,病也好了。
此方,张锡纯命名为“石膏粳米汤”。
不拘古成法
医家应大用
那年,沈阳县知事朱霭亭的夫人50多岁,秋天患了温病,非常严重。朱霭亭是张锡纯的老乡,于是来请。张锡纯到了一看,夫人枕着一个冰袋,头上悬着一个冰袋,愣了。一问才知道,之前是位日本医生用这种方法来退热的,但没有见效。此时,朱夫人闭着眼,昏昏沉沉,人们大声呼喊都没有反应。张锡纯一诊脉,洪大无伦,很有力。他说:这是阳明府热,已达极点。再用冰敷,热向里走,很糟糕。于是张锡纯开始抢救。他就用生石膏4两、粳米8钱,熬出4茶杯,给患者慢慢灌下去。药喝完,患者醒了!张锡纯又开了个清郁热的方子,只服了两剂,病人痊愈。朱霭亭很惊讶,命令公子朱良佐立刻拜张锡纯为师。
自张仲景首先用石膏制方“白虎汤”以来,此方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广泛应用,但石膏的使用再没有开拓。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辩》中,竟给“白虎汤”立下四禁。受吴鞠通影响,医者不敢大胆用石膏,患者也觉得是味猛药。鉴于这些,当时医者就有了“煅用之”的做法。煅用的目的,一是“缓其大寒之性”,二是“煅不伤胃”。张锡纯对此深恶痛绝:“乃自此语一出,直误尽天下苍生矣。”并大声疾呼:“拟成石膏生用直如金丹、煅用即同鸩毒一篇,曾登于各处医学志报”,并言“愚生平志愿,深望医界同仁尽用生石膏,药房中亦皆不鬻煅石膏,乃为达到目的。”“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
张锡纯曾云:“愚临症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症当以数千计。有一症用数斤者,有一症而用至十余斤者,其人病愈之后饮食有加,毫无寒胃之弊。”张锡纯石膏用得巧妙,或大剂量频服,或另研细末送服,或用梨片蘸服,“穷极石膏之功用,恒有令人获意外之效”。古今医者善用石膏者,莫过于张锡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