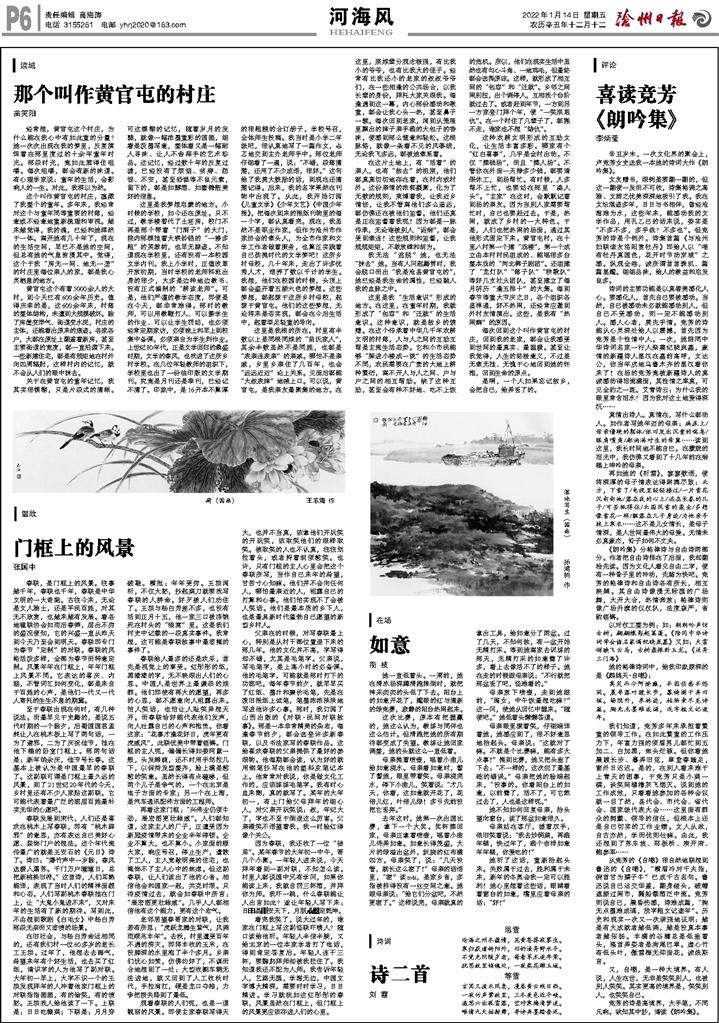经常想,黄官屯这个村庄,为什么能在我心中有如此重的分量?她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反复演绎着在那里度过的十余年童年时光。那段时光,竟如此禁得住咀嚼。每次咀嚼,都会有新的味道。有心理学家说:童年的生活,会影响人的一生。对此,我深以为然。
这个叫作黄官屯的村庄,蕴藏了我整个的童年。多年来,我经常对这个与童年同等重要的村落,经意或不经意地重新梳理和审视。越来越觉得,我的魂,已经和她浑然于一体。离开她有几十年了,现在的生活空间,早已不是她的空间,但总有她的气息弥漫其中。觉得,这个于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村庄里每位亲人的家,都是我心灵栖息的地方。
黄官屯这个有着5000余人的大村,到今天已有600余年历史。值得庆幸的是,这600余年来,村落的整体结构,未遭到大规模破坏。除了房屋变洋气、街道变水泥,村庄的主体,还能看出原来的痕迹。各家各户,大都在原址上翻盖着新房,甚至主要街道的宽度,都一直沿袭下来。一些新建住宅,都是有规矩地在村外向四周辐射,这样村内的记忆,就不会从人们的眼中抹去。
关于在黄官屯的童年记忆,我其实很模糊,只是片段式的清晰。可这模糊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发酵,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国画,细看是泼墨写意,整体看又是一幅耐人寻味、让人不舍释手的艺术珍品。这记忆,经过数十年的反复过滤,已经没有了烦恼、贫瘠、怨恨、不安,甚至恐惧等不良元素,留下的,都是如醇酒、如蜜糖般美好的信息。
这里是我梦想启蒙的地方。小时候的学校,如今还在原址。只不过,教学楼替代了土坯房,校门不再是那个带着“门洞子”的大门,院内那棵挂着大铁铃铛的“一搂多粗”的芙蓉树,也早无踪迹。不知道现在学校里,还有没有一本校园文学内刊。我上小学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学校的老师科班出身的很少,大多是边种地边教书、没有正式编制的“耕读老师”。可是,他们严谨的教学态度,即便是在今天,都非常难得。那时的教师,可以用教鞭打人、可以撕学生的作业、可以让学生罚站,也必须经常定期家访,必须晚上和早上到校集中备课,必须亲自为学生判作业。上世纪80年代,正是文学回归的鼎盛时期,文学的春风,也吹进了这所乡村学校。在几位年轻教师的组织下,学校里也出了一份油印版的文学期刊。究竟是月刊还是季刊,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是16开本不算厚的很粗糙的合订册子,学校号召,全体师生投稿。我当时是小学二年级吧,很认真地写了一篇作文,忐忑地交到主办老师手中。那位老师仔细看了一遍,说:“不错,段落清楚,还用了不少成语,很好。”这句给了我莫大鼓励的话,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后来,我的名字果然在刊物中出现了。从此,我开始订阅《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把每次到来的报纸刊物里的每一个字,都认真看完。现在,我虽然不是职业作家,但作为沧州市作家协会的牵头人,为全市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做着服务,也算正实践着自己孩提时代的文学梦吧!这所乡村母校,几十年来,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我想,他们在校园的时候,头顶上都会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梦想。这些梦想,都起源于这所乡村母校,起源于黄官屯。他们的这些梦想,无论将来是否实现,都会在今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
这里是我根的所在。村里有半数以上是同根同族的“苗氏家人”,其余半数虽然不是同姓,也都是“表亲连表亲”的亲戚。哪怕不是亲戚,乡里乡亲住了几百年,也会“远远近近”论上关系。见面后都能“大叔表婶”地喊上口。可以说,黄官屯,是我亲友最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宗族辈分观念极强,有比我小的爷爷,也有比我大的侄子。经常有比我还小的老家的叔叔爷爷们,在一些相逢的公共场合,以我长辈的身份,拜托大家关照我。每逢遇到这一幕,内心那份感动和敬重,都会让我心头一热,甚至鼻子一酸。每次回到老家,闻到从笼屉里飘出的婶子亲手蒸的大包子的香味,便感到那么惬意和轻松。这根脉络,就像一条看不见的风筝线,无论我飞多远,都被她牵系着。
在这片土地上,有“活着”的亲人,也有“故去”的祖宗,他们都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在村内或村外。这份亲情的浓郁凝聚,化为了无数的规则,束缚着我,让我近乡情怯,让我不管离他们多么遥远,都仿佛还在被他们监督。他们还真是正在监督着我呢!因为都是一脉传承,无论谁被别人“诟病”,都会受到牵连!这些规则和监督,让我规规矩矩,不敢放肆和胡为。
我无法“逃脱”她,也无法“抹去”她。当有人问起籍贯时,我会脱口而出“我是沧县黄官屯的”,她已经是我生命的属性,已经融入我的血脉之中。
这里是我“生活意识”形成的地方。在这里,在童年时期,我就形成了“包容”和“迁就”的生活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故乡的馈赠。在这个传承着中华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村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帮是主流生活态势。它和小市民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态势不同,农民需要在广袤的大地上耕种繁衍,离不开人与人之间、户与户之间的相互帮助。缺了这种互助,甚至会有种不好地、吃不上饭的危机。所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勾心斗角、一地鸡毛,但最终都会选择原谅。这样,就形成了相互间的“包容”和“迁就”。乡邻之间闹别扭,出个调停人,互相找个台阶就过去了。或者赶到年节,一方到另一方家登门拜个年,便“一笑泯恩仇”。在一个村住了几辈子了,都搬不走,谁家也不想“结仇”。
这种农耕文明形成的互助文化,让生活丰富多彩。哪家有个 “红白喜事”,几乎是全村出动。不仅“捧钱场”,而且“捧人场”。不管你在外面一天挣多少钱,都要请假休工,到场帮忙。有时候,人多帮不上忙,也要站在那里“凑人头”。“主家”在这时,会默默记着到场的亲友。因为当别人家需要帮忙时,自己也要赶过去。于是,热闹,就成了乡村的一大特色。于是,人们也把热闹的场面,通过其他形式固定下来。黄官屯村,在十里八村第一个建“戏楼”,第一个成立由本村村民组成的、能唱很多台整本戏的“河北梆子剧团”。还组建了“龙灯队”“落子队”“秧歌队”等好几支社火团队,甚至建立了每月阴历“逢五排十”的大集。每到春节等重大节庆之日,各个组织各显神通,好不热闹,还经常应邀到外村友情演出。这些,是我有“热闹癖”的原因。
每次回到这个叫作黄官屯的村庄,回到我的老家,都会让我感受到世间的最真实、最温暖。甚至让我觉得,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过是无牵无挂、无愧于心地回到她的怀抱,回到生命的原点。
是啊,一个人如果忘记故乡,会把自己,给弄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