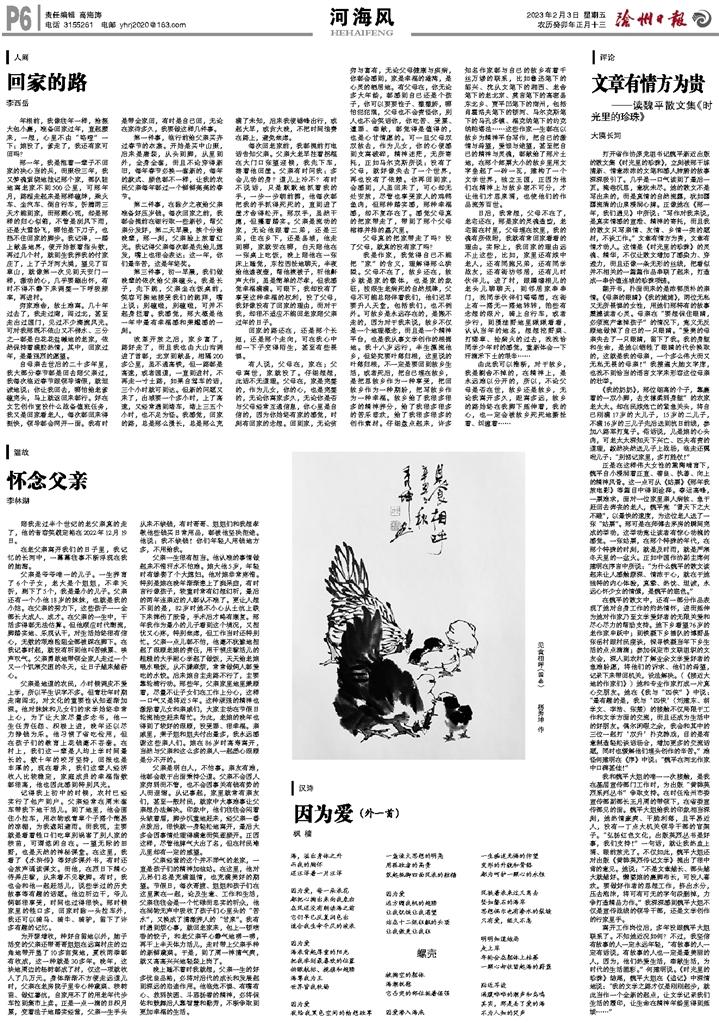陪我走过半个世纪的老父亲真的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定格在2022年12月19日。
在老父亲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我记忆的长河中,一幕幕往事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
父亲是爷爷唯一的儿子。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老大是个姐姐,不幸夭折,剩下了5个,我是最小的儿子。父亲还有一个小他18岁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在父亲的努力下,这些孩子一一全部长大成人、成才。在父亲的一生中,干活多得都无法估算。但他顺应时代潮流,脚踏实地、乐观认干,对生活始终很有信心,无数的艰难险阻全部被踩在脚下。在我记事时起,就没有听到他叫苦喊累、唉声叹气。父亲勇敢地带领全家人走过一个又一个饥寒交困的冬天,让日子越来越舒心。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小时候调皮不爱上学,所以平生识字不多。但青壮年时期走南闯北,对文化的重要性认知逐渐加深。他对妹妹和儿女们的求学始终非常上心,为了让大家尽量多念书,他一生任劳任怨、积极上进,晚年还以尽力挣钱为乐。他习惯了省吃俭用,但在孩子们的教育上花钱毫不吝啬。在村上,我们这一辈是人均上学时间最长的。数十年的咬牙坚持,回报也是丰厚的,现在看来,我们这辈人经济收入比较稳定,家庭成员的幸福指数都很高,他也因此感到特别风光。
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农村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父亲经常在周末套车带我下地干活儿。到了地里,他会固住小拉车,用衣物或青草个子搭个简易的凉棚,为我遮阳避雨。而我呢,主要就是看着牲口们吃草别祸害了别人家的秧苗,可谓悠闲自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也是天然的神秘课堂。在这里,我看了《水浒传》等好多课外书,有时还会放声诵读课文。而他,在烈日下精心侍弄庄稼,从来看不见歇脚。有时,我也会和他一起赶活儿,说些学过的历史故事等有趣的话题。他边听边干,爷儿俩都很享受,时间也过得很快。那时候家里的牲口多,回家时除一头拉车外,我还可以骑马、骑牛、骑驴,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记忆。
为开源增收,种好自留地以外,脑子活变的父亲还带哥哥姐姐在远离村庄的边角地带开垦了10多亩荒地,夏秋两季都有收成,这一种就是30多年。晚年,这块地周边的杨树都成了材,仅这一项就收入了几万元。身体渐渐不方便走远道儿时,父亲在老房院子里专心种蔬菜、秧树苗、做红薯炕,自家用不了的用老年代步车拉到集市上卖。正是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变着法子地踏实经营,父亲一生手头从来不缺钱,有时哥哥、姐姐们和我想孝敬他些钱买日常用品,都被他坚决拒绝。他说:我不缺钱!你们年轻人用钱地方多,不用给我。
父亲一生很有担当。他认准的事情做起来不惜汗水不怕难。娘大他5岁,年轻时有缘娶了个大媳妇。他对娘非常疼惜。特别是娘在晚年渐渐患上了痴呆症,有时言行像孩子,较重时常有幻想幻听,最后的两年连亲近的人都认不准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82岁时她不小心从土炕上跌下来摔伤了股骨,手术后才略有康复。那年我作为最小的儿子看到这个境况,又担忧又心疼,特别焦虑,但工作当时还特别忙。父亲一点儿都不怕,他毫不犹豫地担起了照顾老娘的责任,用干惯庄稼活儿的粗糙的大手耐心学起了做饭,天天给老娘喂水喂饭,从不嫌麻烦,常常做俩人都爱吃的水饺。后来娘自主走路不行了,主要靠轮椅行动。那些年,父亲家里地里兼顾着,尽量不让子女们在工作上分心,这样一口气又是将近5年。这种顽强的精神也激励着儿女和亲戚们,大家主动在节假日轮流抽空赶来帮忙。为此,老娘的晚年也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没受罪、很幸福。亲戚里,荣子姐和姐夫付出最多,我永远感谢这些亲人们。娘在86岁时高寿离开,当然与父亲和这么多的亲人一起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父亲是明白人,不怕事。亲友有难,他都会敢于出面秉持公道。父亲不会因人家穷弱而不管,也不会因事关有钱有势的人而退缩。从记事起,家里就常有亲友们,甚至一般村民,就家中大事难事让父亲想办法解决。印象中,他们往往会闷着头皱着眉,脚步沉重地赶来,经父亲一番点拨后,很快就一身轻松地离开,最后大多会因事情处理得满意而笑逐颜开。正因这样,尽管他脾气大出了名,但在村民堆儿里却有一定的威望。
父亲经营的这个并不洋气的老家,一直是孩子们的精神加油站。在这里,他对儿孙们总是充满温情,也充满美好的期望。节假日,每次哥嫂、姐姐和孩子们在这里聚在一起,论及生意、工作和生活,父亲往往会是一个忙碌而忠实的听众,他在润物无声中吸收了孩子们心里头的“苦水”,又换成了清澈养人的“甘泉”。我有时遇到烦心事,就回老家来,包上一顿喷香的饺子,和老父亲平心静气地唠一唠,再干上半天体力活儿,走时带上父亲手种的新鲜蔬菜。于是,到了周一神清气爽,就又高高兴兴地轻装上岗了。
晚上睡不着时我就想,父亲一生的好多优良品格,必将对后代的成长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启迪作用。他临危不惧、有嘴有心、救弱扶困、斗恶扬善的精神,必将保佑和鼓舞后人靠智慧和勤劳,不断争取到更加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