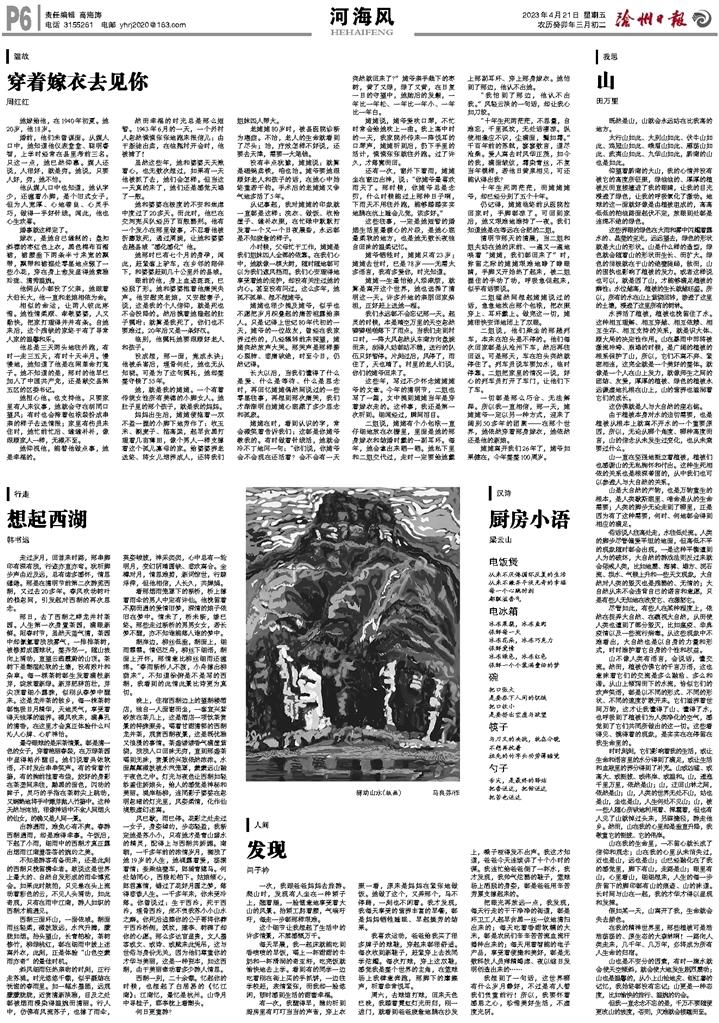既然是山,山就会永远站在比我高的地方。
太行山如此、大别山如此、伏牛山如此、鸡冠山如此、峨眉山如此、雁荡山如此、武夷山如此、九华山如此,黔南的山也是如此。
仰望着黔南的大山,我的心情并没有被它的高度所征服,绿油油的、厚厚的植被反而直接撞进了我的眼睛,让我的目光浸透了绿色,让我的呼吸氧化了激动。地球的这一面就好像是由植被组成的,高高低低的柏油路面起伏不定,放眼到处都是连绵不绝的绿色。
这些养眼的绿色在大雨和雾中闪耀着露水的、晶莹的宝光,远远望去,绿色的形状就是大山的形状。山是什么样的造型,绿色就会随着山的形状而生长、而扩大。绿色的消极就在于山的绝壁陡峭,故而,山的固执也影响了植被的发力。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就是因了山,才能够满足植被的癖性:水位越高,植被的生长就越旺盛。所以,所有的水在山上萦绕回转,渗透了这里的土壤,浸透了这里所有的树林。
水养活了植被,植被也挽留住了水。这种相互理解、相互穿越、相互依赖、相互生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就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决定性作用。山在暴雨中即将被激流冲垮、崩塌的时候,是广阔的植被的根系保护了山,所以,它们不离不弃、紧密相连,这完全就是一个美好的整体。就像是一个人在山上发力,就像师生之间的团结、友爱,厚厚的植被、绿色的植被永远谦虚地扎根在山上,山的营养也滋润着它们的成长。
这仿佛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座右铭。
由于植被本身对水的迫切需要,也是植被从根本上就离不开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哪种高度而言,山的信念从未发生过变化,也从未索要过什么。
山一直在坚强地挺立着植被,植被们也感谢山的无私胸怀和付出。这种生死相依的关系也是根深蒂固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参透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山是大自然的产物,也是万物重生的根本,是人类歇斯底里、唯命是从的生命需要;人类的脚步无论走到了哪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需要,何时、何地都会得到相应的满足。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类的脚步尽管偏爱平坦的地面,但高低不平的现象随时都会出现,一是这种平衡遭到人为的破坏,大自然的游戏法则反过来就会惩戒人类,比如地震、海啸、塌方、泥石流、洪水、气候上升和一些天文现象,大自然对人类的毁灭也是残酷的、无情的;大自然从来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和意愿,只是有些人无知地在改变它、在激怒它。
尽管如此,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在捉弄大自然、在藐视大自然,从而使人类也遭到了部分毁灭,比如瘟疫、非典疫情以及一些流行病毒。从这些现象中不难看出,大自然也是以自身的力量和形式,时时维护着它自身的个性和权益。
山不像人类有语言,会说话,懂交流。然而,植被仿佛它的千言万语,这也意味着它们的交流是多么融洽、多么和谐。从山上倾泻而下的水流,恰似它们的欢声笑语,都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速度扩散开来。它们滋养着世间万物,这才让我懂得了山、懂得了水,也呼吸到了植被们为人类净化的空气,感觉到了它们共同所做出的这一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是实实在在停留在我生命里的。
时时刻刻,它们影响着我的生活,或让生命和语言里的水分得到了满足,或让生活和血液里的养分得到了补充。山或凶猛、或高大、或挺拔、或伟岸、或温和。山,逶迤千里万里,依然是山;山,迂回山林之间,依然是山;山,人类的世界无处不山,站也是山,坐也是山,人生何处不见山;山,被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利用着、挥霍着,但也有人见了山就掉过头来,另辟捷径,游走他乡。然而,山在我的心里却是垂直升降,我敬重它的挺拔、它的伟岸。
山在我的生命里,一不留心就长成了信仰和观念;山在我的心里从未消失过,近也是山,远也是山;山已经融化在了我的感觉里,脚下有山,走路是山;眼里有山,心里看山,细细想来,人生的每一步所留下的脚印都有山的痕迹、山的味道。长时间与山在一起,我的才华才得以显现和发挥。
假如某一天,山离开了我,生命就会失去颜色。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那些植被可是浩浩荡荡的、原生态的大森林啊!一路向人类走来,几千年、几万年,必将成为所有人生命的归宿。
山也是不安分的因素,有时一滴水就会使天空倾斜,就会使大地发生剧烈震动;山也是温馨的,从小上山捡地皮、刨红薯的记忆,我始终都没有忘记;山更是一种态度,比如愉快的旅行、温婉的约会。
但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千万不要随便更改山的坡度,否则,灾难就会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