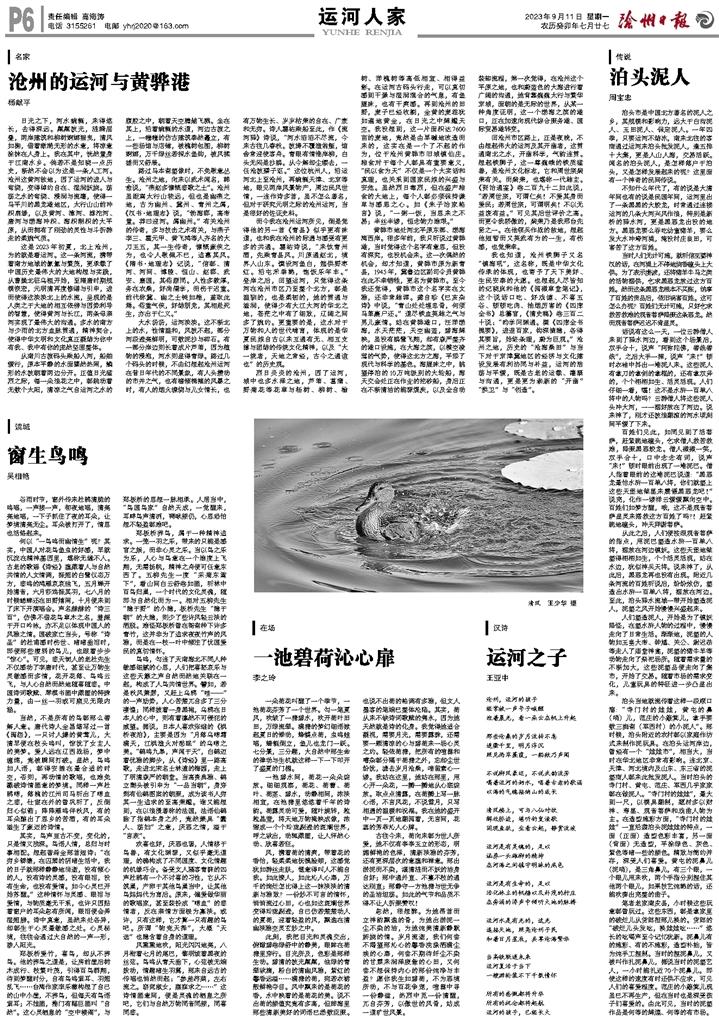谷雨时节,窗外传来杜鹃清脆的鸣唱,一声接一声,彻夜地唱,清亮亮地唱,一下子抓住了夜的耳朵,让梦境清亮无尘。耳朵被打开了,情思也活络起来。
何以“一鸟鸣而幽情生”呢?其实,中国人对花鸟鱼虫的好感,早就沉淀在精神基因里,堪称无缝不入。古老的歌谣《诗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共情的人文情调,振翅的白鹭仪态万方,悲鸣的鸿雁哀哀独飞,五月蝉开始清音,六月莎鸡振其羽,七八月的时候蟋蟀还在田野嬉闹,十月便来到了床下开演唱会。声名赫赫的“诗三百”,仿佛不借花鸟草木之名,羞赧于开口吟咏,亦不足以体现中国人的风雅之情。国破家亡当头,号称“诗圣”的杜甫感时伤世、暗暗垂泪时,即便那些瘦弱的鸟儿,也跟着步步“惊心”。可见,悲天悯人的老杜先生不仅感动了李唐时代,甚至让万物生灵敏感而多情,花开花落、鸟鸣云飞,与人心自然而然地随喜随悲。中国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中藏匿的特殊力量,由一丝一羽或可窥见无限内涵。
当然,不是所有的鸟都那么善解人意。唐代诗人金昌绪写过一首《闺怨》,一只讨人嫌的黄莺儿,大清早便在枝头鸣叫,惊扰了女主人的美梦。爱人远在辽西战场,梦中缠绵,竟被瞬间打破。显然,鸟鸣如人语,都得安插在最合适的时空,否则,再动情的歌唱,也难免戳破诗情画意的梦境。同样一声杜鹃啼,落魄的江州司马听出了啼血之悲,仕宦在外的曾巩听了,反倒归心似箭;阵阵雁鸣伴秋风,有的耳朵酿出了思乡的苦酒,有的耳朵滋生了豪迈的诗情。
其实,鸟声亘古不变,变化的,只是情义浅深。鸟语人情,总归与时事相配。想起普希金那首短诗:“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逝,没有倾心的人,没有诗的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开始苏醒。”这种情怀与灵感、眼泪与爱情,与物质毫无干系,也许只因贴着窗户的耳朵忽有所闻,眼泪便会弄湿翅膀。诗中真意,虽然来处各异,却都生于心灵最敏感之处。心灵秘境,往往会通过大自然的一声一形,渗入阳光。
郑板桥爱竹,喜鸟,却从不养鸟。他的养鸟之道是,让房前屋后树木成行、枝繁叶茂,引得百鸟群翔,待到梦醒时分,自有鸟鸣萦耳、羽翅乱飞……台湾作家李乐薇构想了自己的山中小屋,不养鸟,但每天有鸟语萦耳;不挂画,推门有幅巨画叫“自然”。这心灵栖息的“空中楼阁”,与郑板桥的思想一脉相承。人居当中,“鸟国鸟家”自然天成,一觉醒来,耳畔鸟声清冽,啁啾频仍,心思恐怕想不轻盈都难吧。
郑板桥养鸟,属于一种精神追求。一笼一羽之乐,带来的只能是感官之娱,而非心灵之乐。当以鸟之乐为乐,人心与鸟意在一个维度上飞翔,无需扬帆,精神之舟便可任意东西了。五柳先生一度“采菊东篱下”,看山间白云舒卷如画,听林中百鸟归巢,一个时代的文化灵魂,随即与自然化而为一。相对五柳先生“隐于野”的小隐,板桥先生“隐于朝”的大隐,则少了些许风轻云淡的洒脱。难怪郑板桥曾在衙斋种下许多青竹,这并非为了追求夜夜竹声的风雅,而是在一枝一叶中倾注了忧国爱民的真切情怀。
鸟鸣,勾连了天南海北不同人种敏感细腻的心思,人们把喜怒哀乐与这些天籁之声自然而然地关联在一起,构成了人鸟共情世界。譬如,若是秋风萧瑟,又赶上乌鸦“哇——”的一声助势,人心苦楚兀自多了三分凄惶;同样披着一身黑袍,乌鸦在日本人的心中,则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望。据说,日本人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主要是因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乌啼之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白鹤迈着优雅的脚步,从《诗经》里一路高歌,走进北宋名士林逋的梅园,走上了明清森严的朝堂。当高贵典雅、鹤立潮头被引申为“一品当朝”,身穿刺有仙鹤图案的朝服,成为读书人穷其一生追求的至高荣耀。谁又能想到,在以浪漫著称的法国,法语仙鹤除了指鹤本身之外,竟然兼具“蠢人、荡妇”之意,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欢喜也好,厌恶也罢,人情移于鸟兽,有文化渊源,又似乎毫无道理,的确构成了不同国度、文化情趣的机缘巧合。备受文人骚客青睐的四声杜鹃有一个不讨喜的习性,它从不筑巢,产卵于其他鸟巢当中,让其他鸟妈妈代为育后。原来,偏爱做华丽的歌唱家,甚至装扮成“啼血”的悲情者,反在亲情方面极为寡淡。或许,只有这样,它才算一只有趣的鸟吧。所谓“物竞天择”,大概“天选”也隐含着自身的道理。
风熏熏地吹,阳光闪闪地亮,八月衔着七月的尾巴,黎明续着黑夜的丝弦。鸟鸣从青天垂下,心弦被无端拨动,情趣暗生羽翼,那来自远古的传唱也悄然而起:“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诗情画意间,便是灵魂的栖息之所吧,它们与自然万物同音同频,同喜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