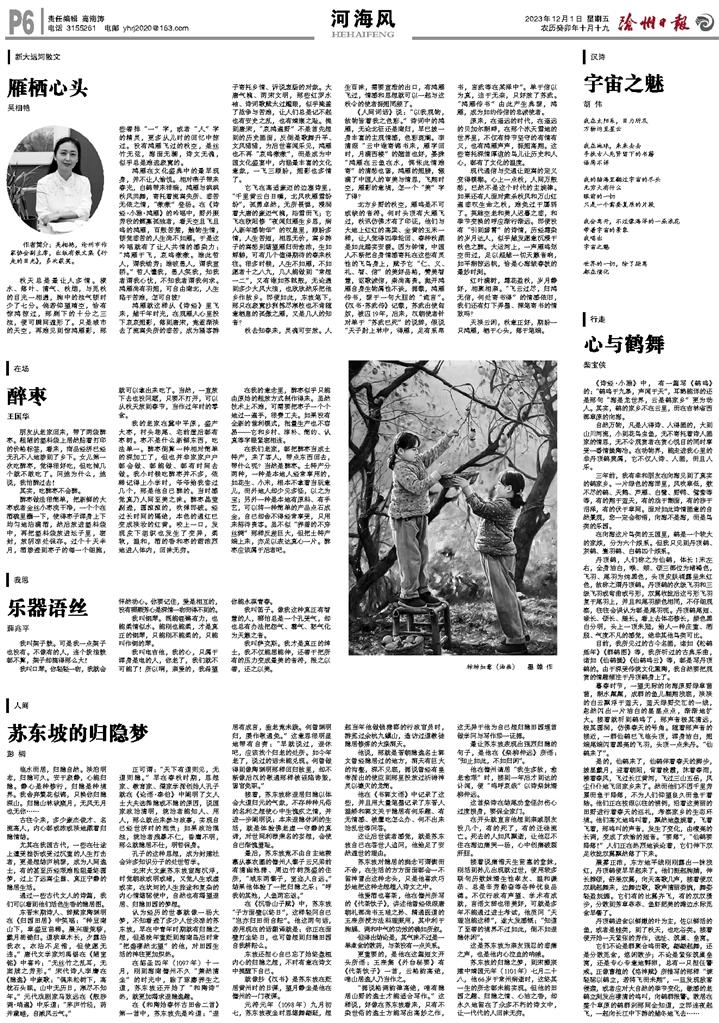秋天总是最让人多情。潦水、落叶、清气、秋烟,与觅秋的目光一相遇,胸中的浊气顿时少了七分。倘若仰望晴空,恰有惊鸿掠过,那剩下的十分之三浊,便可瞬间遁形了。只是城市的天空,再难见到惊鸿雁影,那些善排“一”字,或者“人”字的精灵,更多从儿时的回忆中掠过。没有鸿雁飞过的秋空,是丝竹无弦,海面无澜,诗文无魂,似乎总是难逃寂寞的。
鸿雁在文化盛典中的最早现身,并不让人愉悦。相对燕子带来春光,白鹤带来祥瑞,鸿雁与飒飒秋风共舞,寄托着流离失所、悲苦无依之情,“嗷嗷”登场。在《诗经·小雅·鸿雁》的吟唱中,野外服劳役的鳏寡孤独者,看天空且飞且鸣的鸿雁,百般苦楚,触物生情,顿觉悲苦的人生尚不如雁。于是这吟唱就有了让人共情的感染力:“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哲人懂我,愚人笑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鸿雁尚有羽翅,可自由南北,人生陷于苦难,怎可自拔?
鸿雁就这样从《诗经》里飞来,越千年时光,在观雁人心里投下哀哀翅影,落到唐宋,竟逐渐淡去了流离失所的悲苦,成为骚客游子寄托乡情、诉说衷肠的对象。大唐气魄、两宋文明,那些红罗水袖、诗词歌赋太过耀眼,似乎掩盖了战争与苦难,让人们总是记不起也有安史之乱,也有靖康之耻。提到唐宋,“哀鸿遍野”不是首先想到的历史画面,反倒是歌舞升平、文风猎猎,为后世喜闻乐见,鸿雁也不再“哀鸣嗷嗷”,而是成为中国文化盛宴中,内涵最丰富的文化意象,一飞三顾盼,翅影也多情了。
它飞在高适豪迈的边塞诗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孤勇卓然,无所畏惧,浸润着大唐的豪迈气魄,浴雪而飞;它飞在欧阳修“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的叹息里,顾盼多情,人生苦短,相思无价,离乡游子的离愁别绪望雁归而愈浓,生如蜉蝣,可有几个值得期待的春来秋往。很多时候,人生不如雁,不如愿者十之八九,几人能做到“常想一二”,又有谁如苏轼般,无论遇到多少大风大浪,也欣欣然乐把他乡作故乡。即便如此,东坡笔下,那只在寂寞沙洲拣尽寒枝也不肯随意栖息的孤傲之雁,又是几人的知音?
秋去知春来,灵魂可安放。人生百味,需要宣泄的出口,有鸿雁飞过,情感和思想就可以一起与这秋令的使者振翅同频了。
《人间词话》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诗词中的鸿雁,无论北征还是南归,早已披一身丰富的主观情感,色彩斑斓。李清照“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翘首也好,晏殊“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的清愁也罢,鸿雁的翅膀,缀满了中国人的审美与情思,飞翔时空,雁影的意境,怎一个“美”字了得?
北方乡野的秋空,雁鸣是不可或缺的音符。何时头顶有大雁飞过,秋讯仿佛才有了印证,他们与大地上红红的高粱、金黄的玉米一样,让人觉得四季轮回、春种秋藏是如此踏实安暖。因为钟情,中国人不断把自身情感寄托在这些有灵性的飞鸟身上,赋予它“仁、义、礼、智、信”的美好品格,赞美智慧,讴歌诚信,崇尚高贵。抛开鸿雁自身生物属性不谈,据载,鸿雁传书,源于一句大胆的“诡言”。《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出使匈奴,被囚19年,后来,汉朝使者针对单于“苏武已死”的说辞,假说“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单于信以为真,迫于无奈,只好放了苏武。“鸿雁传书”由此产生典源,鸿雁,成为如约传信的忠诚使者。
原来,在遥远的时代,在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不仅有持节坚守的有情有义,也有鸿雁声声,振翅高翔。这些寄托深情厚谊的鸟儿让历史和人心,都有了文化的温度。
现代通信与交通让距离的定义变得模糊。心上一点秋,人间万般愁,已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还有人面对肃杀秋风和万山红遍悲叹生命之秋,难免过于孱弱了。英雄空老和美人迟暮之悲,和季节变换的呼应渐行渐远。即便没有“引到碧霄”的诗情,历经霜染的岁月达人,似乎越发愿意沉浸于秋色之醉。大运河上,一声雁鸣划空而过,足以超越一切天籁音响,如平湖掠远帆,恰是心海皱春波的最妙时刻。
红叶满树,霜花盈秋,岁月静好,相聚相亲。“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的情感依旧,我们还有灯下弄墨、挥笔寄书的情致吗?
天淡云闲,秋意正好,期盼一只鸿雁,栖于心头,落于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