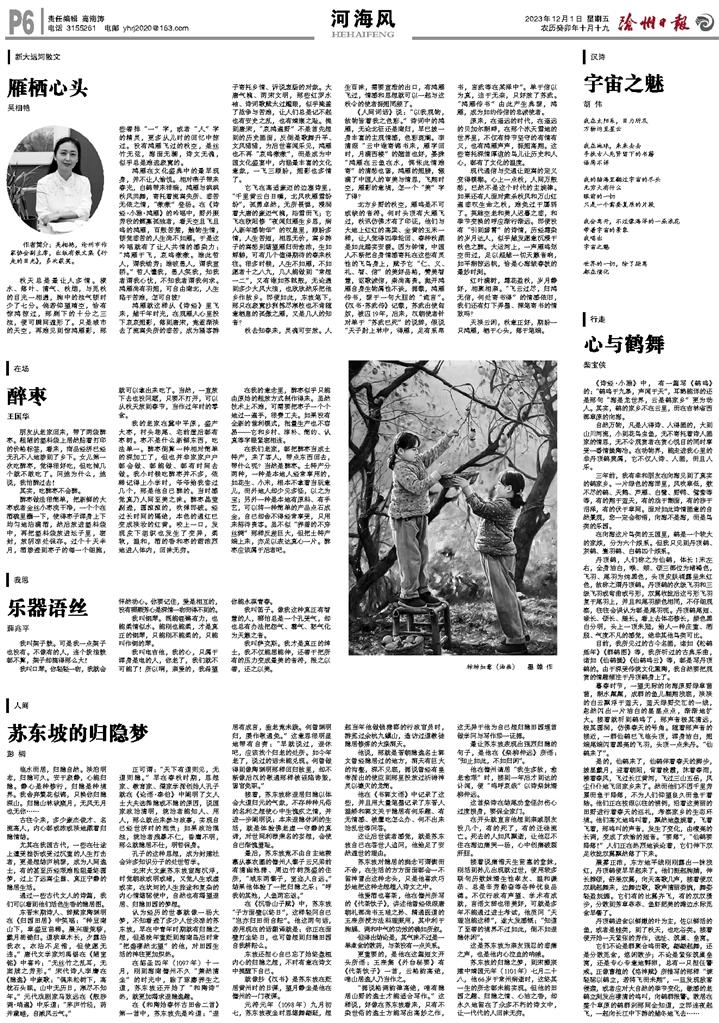临水而居,归隐自然。淡泊明志,归隐可久。安于寂静,心能归隐。静心是种修行,归隐是种境界。我舍弃繁花似锦,只换你归隐深山。归隐山林欲窥月,无风无月也无你……
古往今来,多少豪杰俊才、名流高人,内心都或浓或淡地藏着归隐情结。
尤其在我国古代,一些在仕途上遭受挫折或受过沉重的人生打击者,更是想结庐桃源,成为人间逸士,有的甚至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圆梦,过上了远离尘嚣、真正宁静的隐居生活。
通过一些古代文人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活色生香的隐居图。
东晋末期诗人、辞赋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笑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喜吟:“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宋代诗人李膺在《隐逸》中豪歌:“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元代戏剧家马致远在《般涉调·哨遍》中乐道:“茅庐竹径,药井蔬畦,自减风云气。”
正可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早在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在《论语·泰伯》中阐明了文人士大夫选择隐或不隐的原因,说国家政治清明,统治者能知人、用人,那么就出来参与政事,实现自己经世济时的抱负;如果政治混浊,统治者残暴不仁,昏庸不明,那么就隐居不仕,明哲保身。
孔子的这种思想,成为封建社会许多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宦海沉浮,时觉朝政或明或暗,又觉人生或虚或实,在坎坷的人生旅途和复杂的内心情绪驱使中,自然也有渴望退居、归隐田园的梦想。
认为经历的世事就像一场大梦,不知看透了多少人世炎凉的苏东坡,早在中青年时期就有归隐之想,但是晚年重贬到海南岛后时常“把盏凄然北望”的他,对田园生活的神往更加炽热。
在绍圣四年(1097年)十一月,刚到海南儋州不久“萧然清坐”的时光中,除了琢磨养生之道,苏东坡还开始了“和陶诗”热,就更加渴求退隐逸趣。
在《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第一首中,苏东坡先是吟道:“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践。何曾渊明归,屡作敬通免。”这意思很明显地带有自责:“早就说过,退休吧,应该找个归老的处所。如今年老了,说过的话未能兑现。何曾做得到像陶渊明那样回归故里,却不断像后汉的敬通那样被诬陷谗毁,罢官免职。”
接着,苏东坡称退居归隐以体会大道归元的气象,不存种种凡俗的名利之想使心中生愧疚之情,并进一步阐明说:本来退隐休闲的生活,就是体验佛老虚一守静的真谛,对世间利禄荣名的妄想,会使自己惭愧羞耻。
最后,苏东坡竟不由自主地羡慕从事农圃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前有清幽池塘、周边竹树茂盛的住所,“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结果他体验了一把归隐之乐:“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
在《沉香山子赋》中,苏东坡“子方面壁以终日”,这样轻问自己“岂亦归田而自耘”。他这两句话,若用现在的话翻译就是:你正在面壁打坐终日,也可曾想到归隐田园自我耕耘么。
东坡还担心自己忘了始终盘桓内心的归隐之想,不时有意在诗文中提醒下自己。
就像抄《汉书》是苏东坡在贬居黄州时的日课,望月静坐是他在儋州的一门夜课。
元符元年(1098年)九月初七,苏东坡夜坐时思绪舞翩跹,想起当年他做钱塘郡的行政官员时,游览过余杭九鏁山,造访过道教徒隐居修炼的大涤洞天。
他说,那就是晋朝隐逸名士郭文曾经隐居过的地方,洞天有巨大的沟壑,深不见底,据说曾经有皇帝派出的使臣到那里投放过祈祷神灵以禳灾的龙简。
他在《书郭文语》中记录了这些,并且用大量笔墨记录了东晋人温峤和郭文关于隐居有何乐趣、有无情感、被鹰吃怎么办、何不出来治乱世等问答。
这让后世读者感觉,就是苏东坡自己在答世人追问,他给足了安然遁世的理由。
苏东坡对隐居的痴念可谓锲而不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一不留神冒出这种念头,只是他喜欢巧妙地把这种念想植入诗文之中。
他爱酒也喜茶,他在儋州所写的《代茶饮子》,讲述他曾经依照唐朝礼部尚书王珪之孙、精通医道的王焘所授方法料理服用,其中利于胸膈、调和中气的功效的确如所叙。
但得出结论是,其气味不过是一单煮食的散药,与茶没有一点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篇短文开头所语:王焘集《外台秘要》有《代茶饮子》一首,云格韵高绝,唯山居逸人乃当作之。
“据说格调韵律高绝,唯有隐居山野的逸士才能适合写作。”这样说,好像在苏东坡看来,只有不染世俗的逸士方能写出高妙之作,这无异于他为自己想归隐田园埋首做学问与写作添一证据。
最让苏东坡表现出强烈归隐的句子,是他在《祭柳仲远》所语:“知止如此,不如归闲”。
他在儋州谪居“我生多故,愈老愈艰”时,接到一年后才到达的讣闻,便“呜呼哀哉”以诗祭妹婿柳仲远。
这首祭诗在结尾劝堂侄勿伤心过度损身,要保全家门。
在开头就直言他想到亲戚朋友没几个,有的死了,有的迁徙流亡。死去的人如风飘逝,让他忍不住在海边痛哭一场,心中创痛破裂肝胆。
接着说痛惜天生贤惠的堂妹,刚活到孙儿出现就过世,便用较多联句历数妹婿生性孝友、温和谦恭、总是辛劳勤奋等各种优良品德。不仅行政有声望、学术有成就,言语文辞也很美好,可就是多年不能通过进士考试,他质问“天理岂能这样”,遂大发感慨:“知道了至善的境界不过如此,倒不如退隐休闲”。
这是苏东坡为亲友强忍的悲痛之声,也是他内心泣血的呐喊。
苏东坡的归隐之梦,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他66岁于常州病逝时,这终其一生的所念都未能实现。但他的田园之趣、归隐之情、心洁之香,却永久地留在了众多不朽的诗文中,让一代代的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