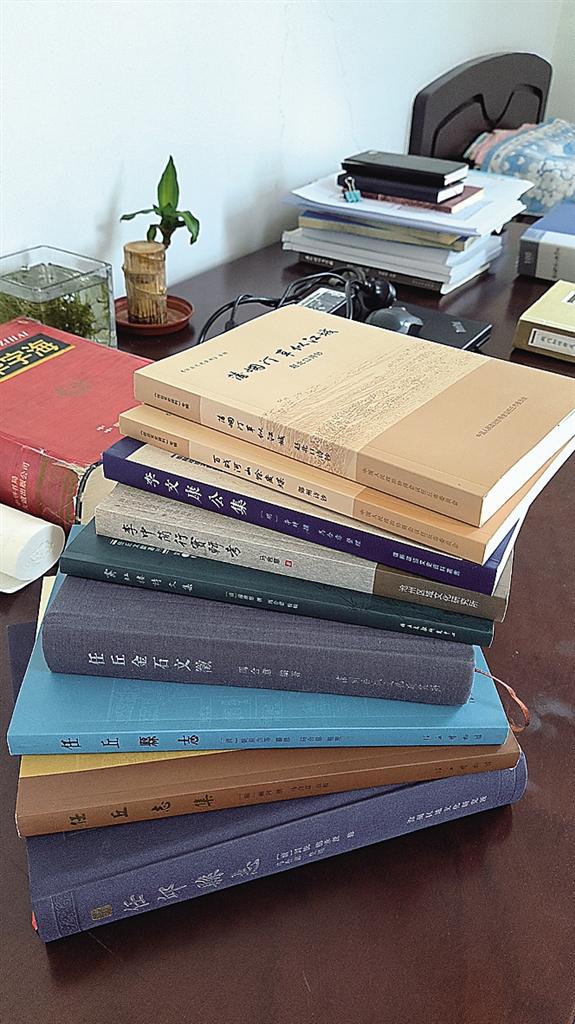近日,由马合意整理的明代大学士李时的《李文康公集》正式结集成册,填补了任丘明代阁臣群体研究的一项空白。30多年来,马合意积极参与任丘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先后整理了18种地方文献典籍。其中,马合意点校整理的明代万历及清代康熙、乾隆、道光等历史时期的任丘县志横排简体版,成为了解任丘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由他编写的《任丘金石文征》与任丘县志相互补充、互为借鉴,更成为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参考书籍。
15岁少年
爱上古朴线装书
记者:30多年来,您一直坚持在做整理家乡文化史的工作,您是如何走上文史研究之路的?
马合意:我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热爱始于对文物和考古的兴趣。初中时期,我有幸遇到了黄秋华老师,他是当时任丘首屈一指的文物研究者,也是我在初中的文史导师。黄老师退休后,被任丘市文化局聘请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顾问。由于老师的指导和影响,我得以明白地方文献与地方出土文物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为后来参与任丘市博物馆建设及展陈奠定了基础。
我在17岁时离开了学校,但仍坚持每周去找老师借书,除考古与文物方面的书籍外,其中较为珍贵的是乾隆版《任邱县志》和道光版《任邱续志》,我用3年的时间把它们抄写下来。抄书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也加深了我对家乡历史的热爱。后来,我到了任丘文保所工作,这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从事地方文史的整理与研究。就这样,我从一个考古与文史的业余爱好者,逐渐成为一个以文献整理为专职工作的专业人员。
记者:去年,您主动辞去了任丘博物馆馆长的职务,成为任丘文献研究中心负责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文史整理研究的事业中。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马合意:对我而言,最大的乐趣源于探索和分享文史的奥秘。发掘那些隐藏的、少为人知的文献,并逐步将它们收集、整理,使这些知识向大众公开、为更多人所了解,会很有成就感。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如同找到珍宝,给我带来无尽的喜悦。我的记忆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比如完成一本书、有了一项新发现,那种成就感溢于言表。来到任丘文献研究中心后,我每天都在办公室中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快乐已变成日常,每一天都沉浸在这样的快乐中。
整理出家乡人
能读懂的文化史
记者:多年来您著述颇丰,很多都是鸿篇巨帙,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研究成果?
马合意:现在整理的约300万字的地方文献典籍中,最重要的还应该是万历、康熙、乾隆、道光四个历史时期任丘县志点校本。之所以要点校这四种县志,有两个原因:一是原书为清代刊刻的古籍,竖排繁体,不易阅读,且数量稀少,大部分人无法接触到。虽在2005年进行了一次影印,但影印本由于价格昂贵、普及度低,导致人们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受限。二是我始终认为,县志作为了解地方历史的首要资料,具有权威性和必要性。因此,我决定优先整理县志,让更多研究者和读者能尽快更方便地了解地方历史的梗概,进而深入研究地方历史的某一领域。
目前,四种县志已全部整理完成,采用横排简体加标点的形式,无偿提供给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目的就是为大家轻松了解家乡历史文化提供一个无障碍入口。
在整理的资料中,我投入时间和心血最多的是《任丘金石文征》。这本书的汇集整理历时近20年,从15岁开始关注金石文字到2012年结集,收录约300多篇作品、约35万字。
这本书的内容除对先前县志中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起到了补充作用外,对于外地古籍整理者和金石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例如沈阳孙植先生在整理明人《孙承宗集》时,于书中辑出未见《高阳集》的文章数篇。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的马振颖老师在金石研究工作中也曾经利用过这本书上所收的文献资料。
记者:整理地方文献对弘扬宣传地方文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马合意:由我点校的著名清代学者、诗人边连宝的学术笔记《病馀长语》,记录了作者大量的诗学理论。我用了3年时间,校对了300多种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引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老师在撰写《清代诗学史》第二卷时,曾数次引用,今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河北大学文学院刘青松老师在辑校《坳堂诗文集》时,也进行了征引。这种引用其实也是地方文化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对于弘扬地方文化很有意义。
还有就是对明代嘉靖时期的大学士李时文集的整理,由于李时的诗文集今已散失,故此书全部是辑佚而成。李时官至内阁首辅大学士,卒谥文康,他是明代沧州籍人里官职最高的。他是鄚州人,和我同乡,我从小就接触他的家族遗迹。李时对任丘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在吏部尚书任内挑选能人治理任丘,推动了任丘教育和城市建设,对任丘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任丘的第一本县志,也是由他促成编纂的。
2015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访问学者,参与2013年度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课题,承担了清代文学家李中简事迹编年撰写任务。之后又将此扩充为《李中简行年辑考》,用文献资料细致再现了李中简的生平事迹。李中简作为“河间七子”之一,在乾隆时期的文坛上产生过影响,他是乾隆皇帝第五子永琪的老师,和纪晓岚同受乾隆帝喜爱。今存其所著《嘉树山房诗集》十八卷、《文集》五卷。这本《李中简行年辑考》,将来会对李中简的诗学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深挖乡邦文献
推广地域文化
记者:整理地方文献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马合意:在整理地方文献的过程中,除了资金困难之外,最难的是“找书”,很多所需古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我在寻找李时的墓志铭时,辗转多地。找到后发现内容不全,还需继续寻找,于是,我又跑到天津图书馆才查阅完整。此外,有些书籍虽知其所在,却不对外开放或不允许借阅。前几天,我到山东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乡邦文献时,得到了图书馆老师们的帮助,获得了所需资料,在这么多年的搜集资料过程中,这是最为顺利和愉悦的一次。总的来说,搜集乡邦历史文献资料的过程,既耗时费财又充满种种困难与波折,每获取一份资料都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但同时也获得了无比的快乐。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对前人著述错误的甄别。在整理古代文献时,常常会遇到前人的作品存在错误或需修订的情况。因此,了解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至关重要,它们能帮助研究者辨别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及其优缺点。比如乾隆二十七年所修的《任邱县志》,其初印本极为罕见,而常见的是道光十七年的后印本。原因是乾隆版《任邱县志》内多有触及清廷忌讳的“虏”“夷狄”“丑虏”等敏感词汇。书版刊刻后,恐触文字之狱,故印刷不多。至道光十七年,刊印《任邱续志》时,将当时流传不多的乾隆版《任邱县志》内的忌讳字词进行了“挖改”,与道光续志一同印刷。这种做法反映了历史时代的文化审查,体现了对清廷政权的迎合。因此,在整理县志的过程中,找到乾隆初印本,与道光后印本相互校勘,还原乾隆县志的真实记载,从而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是研究古籍文献资料的关键。
记者:任丘地区的历史文化,在沧州乃至全国范围内有何特殊地位或显著特点?
马合意:古代文化载体多种多样,但一个重要的依托便是历史文献典籍。十几年前,我曾参与《历代沧州诗选粹》的编辑工作,跑遍京津冀各大图书馆,对整个沧州现存的历代别集做了全面梳理,发现任丘古典文献存世量有130余种之多,这个数量不仅位居沧州之首,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是排名靠前的,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县,这与其全国百强县的地位也相匹配。而且诸如清代的庞垲、边连宝、李中简、边浴礼等人,都在当时北方地区乃至全国有着广泛的文学影响力,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您对沧州本地文史研究有何建议?
马合意:沧州的历史文化研究,我觉得首要任务是深入挖掘和整理历史文献,这是所有后续工作的基石。无论是研究、传承、传播还是保护,都必须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否则,如果缺乏全面的历史文化重现,仅凭一鳞半爪的信息去阐述或传播,可能会导致可信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