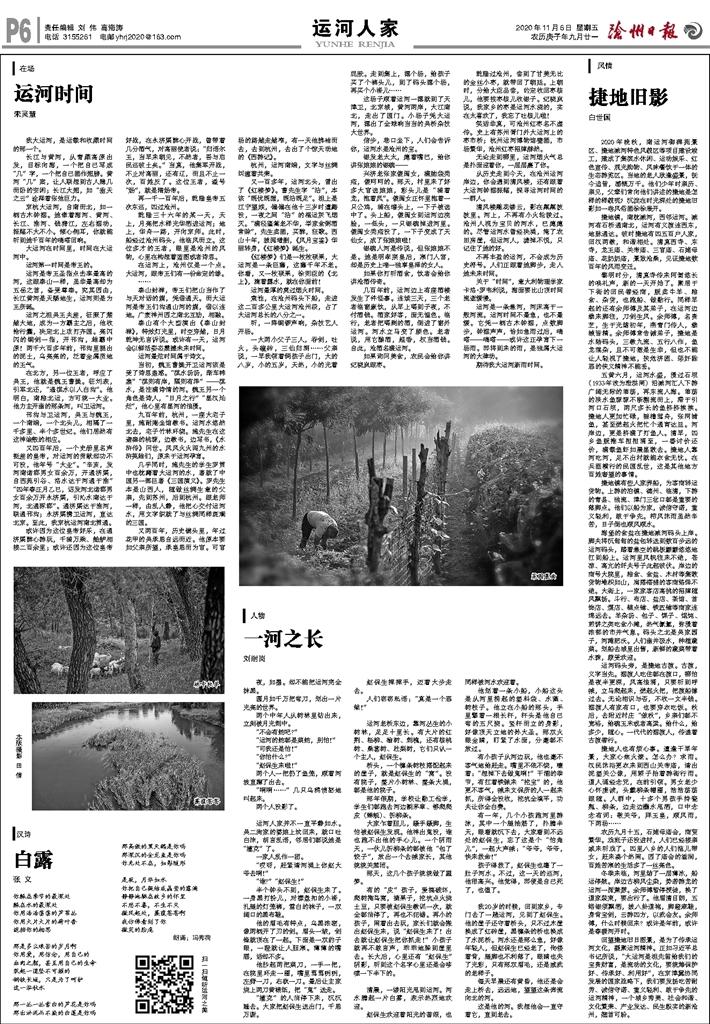风情
2020年晚秋,南运河御碑苑景区、捷地减河特色风貌区等项目建设竣工,建成了集滨水休闲、运动娱乐、红色宣传、观光购物、风味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游览区。当地的老人欣逢盛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们少年时亲历、亲见,父辈们常向他们讲述的捷地是怎样的样貌呢? 沉淀在时光深处的捷地旧影如一卷风俗画徐徐展开。
捷地镇,南枕减河,西邻运河。减河有石桥通南北,运河有义渡连西东,地脉通达。彼时捷地有四五百户人家,回汉两教,和谐相处。清真西寺、东寺,龙王庙、关帝庙、三官庙、石姥母庙、花奶奶庙,景致沧桑,见证捷地数百年的风雨变迁。
黎明时分,清真寺传来阿訇悠长的唤礼声,新的一天开始了。聚居于下街的回民善经商,贩卖牛羊、粮食、杂货,也跑船、做勤行。同样早起的还有余师傅及其弟子,在运河边拳来脚往,刀剑生风。余师傅,名贵芝,生于光绪初年,燕青门传人,拳械皆精。余师傅常告诫弟子,捷地是水陆码头,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鱼龙混杂,且不可惹是生非,但也不能让人轻视了捷地,扶危济困、惩奸除恶的侠义精神不能丢。
五黄六月,运河水盛,漫过石坝(1933年改为泄洪闸)沿减河汇入下游广阔无际的苇荡,再东流入海。苇荡的淡水鱼源源不断溯流而上,滞于引河口石坝,两尺多长的鱼挤挤挨挨。捷地人更加忙碌,摇橹驾舟,张网捕鱼,甚至燃起火把忙个通宵达旦。河岸边,更是挤满了打鱼人。清早,四乡鱼贩推车担担涌至,一番讨价还价,满载鱼虾如晨星散去。捷地人靠河吃河,足不出村就能衣食无忧。在兵匪横行的民国乱世,这是其他地方百姓奢望的事情。
捷地镇有些人家养船,为客商转运货物。上游的泊镇、德州、临清,下游的青县、独流、津门三岔口都是重要的落脚点。他们以船为家,诚信守诺,重义轻利,敢于争先。栉风沐雨虽然辛苦,日子倒也顺风顺水。
海堡的食盐在捷地减河码头上岸。脚夫将沉甸甸的盐包转送到数百步远的运河码头,踏着悬空的跳板颤颤悠悠地扛到船上。运河里风帆往来不绝,苍凉、高亢的纤夫号子此起彼伏。岸边的商号大院里,粮食、食盐、木材等集散货物堆积如山,肩搭褡裢的客商络绎不绝。大街上,一家家客店高挑的招牌随风飘扬。斗行、布店、盐店、茶馆、首饰店、煤店、糕点铺、铁匠铺等商家连绵远去。羊杂汤、包子、馃子、馄饨、煎饼之类吃食小摊,热气氤氲,弥漫着浓郁的市井气息。码头之北是吴家园子,河滩肥沃。人们凿井汲水,种植蔬菜。划船去城里出售,新鲜的蔬菜带着水珠,颇受欢迎。
运河码头旁,是捷地古渡。古渡,义字当先。摆渡人吃住都在渡口,哪怕是夜半更深,风高浪涌,只要听到呼喊,立马爬起来,燃起火把,把渡船撑过去。无论相识与否,不收一文半钱。摆渡人有家有口,也要穿衣吃饭。秋后,去附近村庄“敛秋”,乡亲们都不宽裕,给碗玉米或者高粱。给什么,给多少,随心。一代代的摆渡人,传递着古渡善行。
捷地人也有烦心事。遭逢干旱年景,大家心焦火燎。怎么办?求雨。汉民沐浴更衣来到西山关帝庙,请出泥塑关公像,用轿子抬着游街行雨。道人诵经念咒,在前引领。男女老少心怀虔诚,头戴柳条帽圈,浩浩荡荡跟随。人群中,十多个男孩手持瓷瓶、柳条,边走边蘸水甩洒,口中念念有词:敬关爷,拜玉皇,顺风雨,下两场……
农历九月十五,石姥母庙会,商贸繁华。戏班子还没进村,人们已经接亲戚来听戏了。四里八乡的人们拖儿带女,赶来凑个热闹。因了庙会的滋润,百姓苦寒的生活多了一丝亮色。
冬季来临,河里结了一层薄冰,船运停航。岸边古柳风尘染,势若游龙的运河一派萧瑟。余师傅暂停授徒,换了道家装束,要出行了。他眉清目朗,五绺银须飘洒,披八卦道袍,脚蹬麻鞋,身背宝剑,云游四方,以武会友。余师傅,什么时候回来?或许是年前,或许是春暖河开时。
回望捷地旧日图景,是为了传承运河文化,凝聚运河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我们要发扬吃苦耐劳、诚信守诺、重义轻利、敢于争先的运河精神,一个城乡秀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产业发达、民生殷实的新沧州,翘首可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