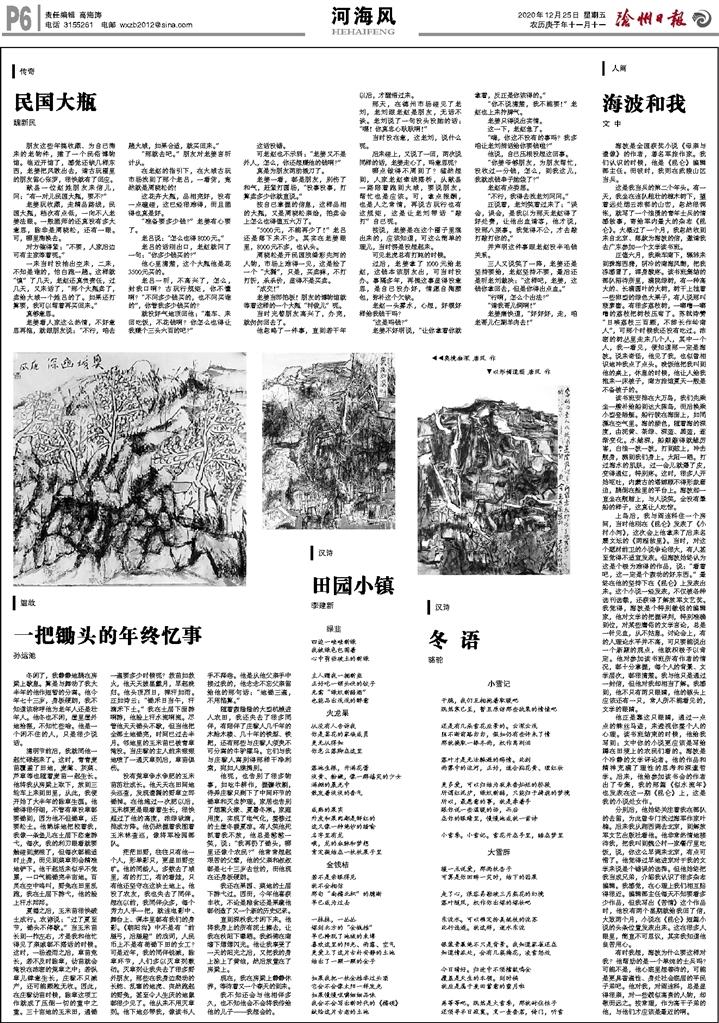海波是全国获奖小说《母亲与遗像》的作者,著名军旅作家。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昆仑》编辑部主任。而彼时,我则在武陵山区当兵。
这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有一天,我坐在连队粗壮的樟木树下,望着远处烟云浓郁的山峦,忽然很惆怅,就写了一个浪漫的青年士兵的情感故事,寄给军内最大的杂志《昆仑》。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忽然收到来自北京、落款为海波的信,邀请我去广东参加一个文学读书班。
正值六月,我乘车南下,辗转来到珠海西塘,阴冷的南海风潮,把我冻感冒了,浑身酸疼。读书班集结的部队招待所里,满院绿树,有一种高大的、长满圆叶的大树,树干上挂着一些卵型的绿色大果子,有人说那叫菠萝蜜。有很多荔枝树,一嘟噜一嘟噜的荔枝把树枝压弯了。苏轼诗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过。浓密的树丛里走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我一看见,便知道那一定是海波。说来奇怪,他见了我,也似曾相识地冲我点了点头。晚饭他把我叫到他的桌上,休息的时候,他让人给我抱来一床被子,南方旅馆夏天一般是不备被子的。
读书班安排在大万岛,我们先乘坐一艘补给船到达大陈岛,而后换乘小型登陆艇。船行驶在海面上,如同漂在空气里。海的颜色,随着海的深度,由泥黄、茶绿、深蓝、黑蓝,逐渐变化。水越深,船颠簸得就越厉害,白浪一波一波,打到舷上,冲击舰身,溅到我们身上。太阳一晒。打过海水的肌肤,过一会儿就爆了皮,变得通红,特别疼。这时,很多人开始呕吐,内蒙古的塔娜顾不得形象窘迫,躺倒在舱里的平台上。海波却一直坐在舰艏上,与人说笑,全没有晕船的样子,这真让人吃惊。
上岛后,我与阎连科住一个房间,当时他刚在《昆仑》发表了《小村小河》,这次会上他拿来了后来名震文坛的《两程故里》。当时,对这个题材前卫的小说争论很大,有人甚至觉得不适宜发表。但海波始终认为这是个极为难得的作品,说:“看着吧,这一定是个轰动的好东西。”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在《昆仑》上发表出来。这个小说一经发表,不仅被各种选刊选载,还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奖。我觉得,海波是个特别敏锐的编辑家,他对文学的把握评判,特别准确到位,对某些庸俗的文学言论,总是一针见血,从不姑息。讨论会上,有的人理论水平并不高,可只要能说出一个新颖的观点,他就积极予以肯定。他对参加读书班所有作者的情况,都十分掌握,每个人的背景、文学层次,都很清楚。我与他只是通过一封信,但他对我却相当了解。我感到,他不只有两只眼睛,他的额头上应该还有一只,常人所不能看见的,文学的眼睛。
他正是靠这只眼睛,通过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来透视你整个人的心理。读书班结束的时候,他给我写到:文中你的小说更应该是写给蹲在田埂上的农民们看的。海波是个冷静的文学评论者。他的作品和精神充满了理性的思考和深邃哲学。后来,他给参加读书会的作者出了专集,我的那篇《似水流年》也发表在这一期《昆仑》上,这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分别后,他始终关注着我在部队的去留,为此曾专门找过海军作家叶楠。后来我从湘西调去北京,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看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把我叫到魏公村一家餐厅里吃饭,说,你这么早调来北京,有点可惜了。他觉得过早地进京对于我的文学来说是个错误的选择。但他始终把我当成兄弟,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杂志编辑。我感觉,在心理上我们相互贴得很近。编辑部主任每天不知要看多少作品,但我写出《苦情》这个作品时,他没有两个星期就给我回了信,大致两个月,小说在《昆仑》短篇小说的头条位置发表出来。这在很多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其实我知道他良苦用心。
有时我想,海波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帮助的是一个单纯的士兵吗?可能不是,他心底里想善待的,可能是更具普遍性、身处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吧。他对我,对阎连科,总是显得很亲,对一些貌似高贵的人物,却敬而远之。按常理,作为高干子弟的他,与他们才应该是最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