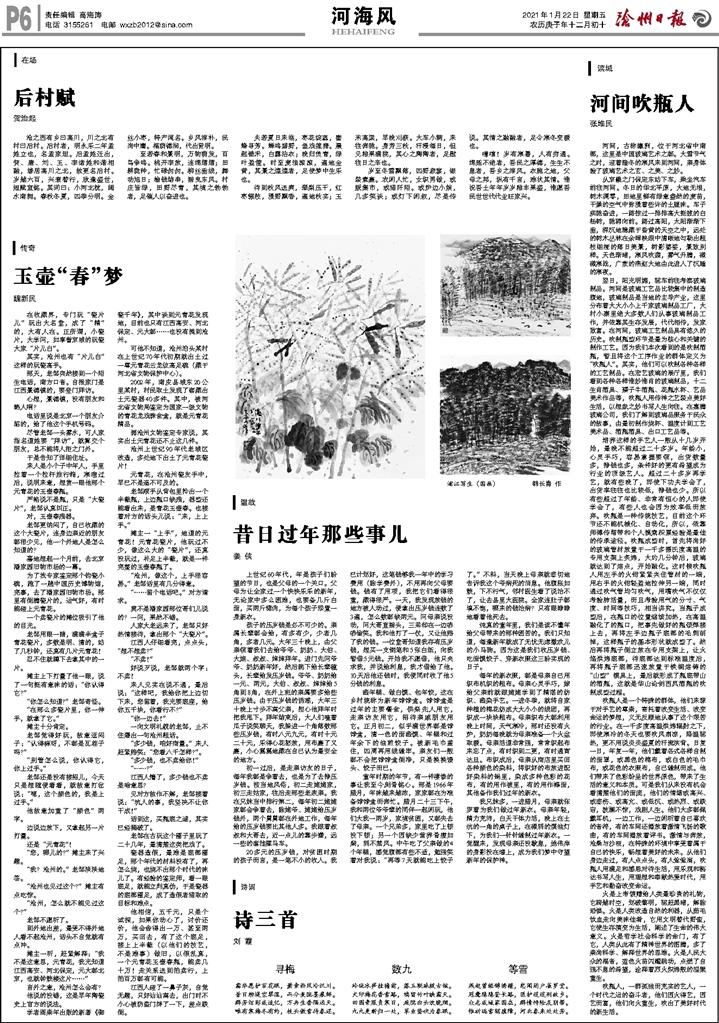上世纪60年代,年是孩子们盼望的节日,也是父母的一个关口。父母为让全家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新年,无论家中多么困难,也要备几斤白面,买两斤猪肉,为每个孩子添置一身新衣。
孩子的压岁钱是必不可少的。亲属长辈都会给,有多有少,少者几角,多者几元。大年三十晚上,由父亲领着我们去给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叔叔、婶婶拜年。进门先问爷爷、奶奶新年好,然后跪下给长辈磕头,长辈给发压岁钱。爷爷、奶奶给一元、两元,大伯、叔叔、婶婶给5角到8角,在外上班的亲属要多给些压岁钱。由于压岁钱的诱惑,大年三十晚上寸步不离父亲,担心他拜年时把我甩下。拜年结束后,大人们嗑着瓜子说笑聊天,我躲进一个角落数那些压岁钱,有时八元九元,有时十元二十元,乐得心花怒放,用布裹了又裹,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初一过后,是走亲访友的日子,每年我都是争着去,也是为了去挣压岁钱。按当地风俗,初二走姥姥家,初三走姑家,往后走那些老表亲。我在兄妹当中排行第二,每年初二姥姥家都会争着去,除姥爷、姥姥给压岁钱外,两个舅舅都在外地工作,每年给的压岁钱要比其他人多。我跟着叔叔和大哥去,近一点儿的靠步撵,远一些的套挂骡马车。
20多元的压岁钱,对贫困时期的孩子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已计划好,这笔钱够我一年中的学习费用(除学费外),不用再向父母要钱。钱有了用项,我把它们看得很重,藏得很严。一天,我发现放钱的地方被人动过,便拿出压岁钱连数了3遍,怎么数都缺两元。问母亲说没动,问大哥直摇头,三弟却在一边哧哧偷笑。我和他打了一仗,又让他赔了我的钱。一位堂哥知道我存有压岁钱,想买一支钢笔和5张白纸,向我暂借5元钱。开始我不愿借,他只央求我,并说给利息,我才借给了他。10天后他还钱时,我便同时收了他5分钱的利息。
蒸年糕、做白馍、包年饺,这在乡村统称为新年饽饽盒。饽饽盒是过年的主要餐食,供祭先人用它,走亲访友用它,招待亲戚朋友用它。正月初二,似乎满世界都是饽饽盒,清一色的面蒸馍、年糕和过年余下的油煎饺子。被新毛巾盖住,四周再用线缝牢。亲友们一般都不会把饽饽盒倒净,只是换换馒头、饺子而已。
童年时期的年节,有一件凄惨的事让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1966年腊月,年味越来越浓,家家都在为准备饽饽盒而奔忙。腊月二十三下午,我和两位爷爷辈的同伴一起闲玩,他们大我一两岁,家境贫困,又都失去了母亲。一个兄弟多,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另一个因缺少营养骨瘦如柴,弱不禁风。中午吃了父亲做的4个年糕,感觉腹部有些不适,勉强笑着对我说:“再等7天就能吃上饺子了。”不料,当天晚上母亲就悲切地告诉我这个爷病死的消息。他腹胀如鼓,下不行气,邻村医生看了说治不了,让去县里大医院。全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来的钱治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纯真的童年里,我们是读不懂年给父母带来的那种困苦的。我们只知道,每逢新年就成了无忧无虑撒欢儿的小马驹。因为这是我们收压岁钱、吃面馍饺子、穿新衣服这三盼实现的日子。
每年的新衣服,都是母亲自己用织布机织的粗布。母亲心灵手巧,嫁给父亲前就跟姥姥学到了精湛的纺织、蒸染手艺。一进冬季,就将自家种植的棉花纺成大大小小的线团,再织成一块块粗布。母亲织布大都利用晚上时间,天气寒冷,那时还没有火炉,奶奶每晚就为母亲准备一个火盆取暖。母亲活道非常强,常常织起布来忘了点,有时织到二更,有时通宵达旦。布织成后,母亲从商店里买回各种颜色的染料,将织好的布放进配好染料的锅里,染成多种色彩的花布,有的用作被里,有的用作褥面,其他备作我们过年的新衣。
我兄妹多,一进腊月,母亲就张罗着为我们做过年新衣。母亲年轻,精力充沛,白天干体力活,晚上在土炕的一角的桌子上,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为我们一针针缝制过年新衣。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没歇息,她伟岸的身影投在墙上,成为我们梦中守望新年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