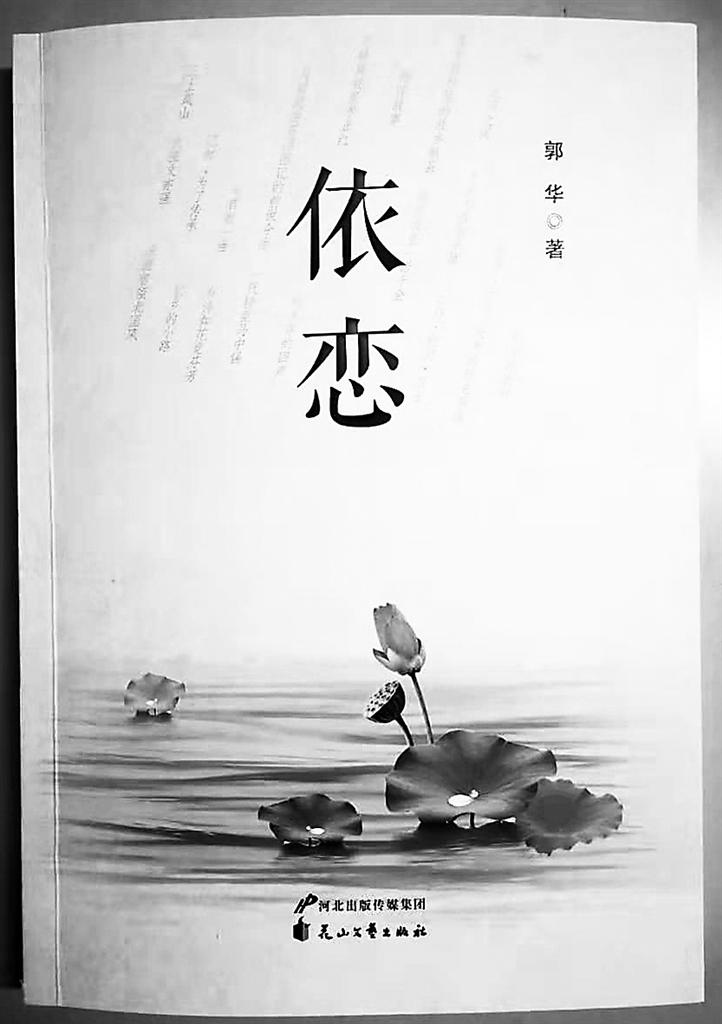编者按:
郭华的散文随笔集《依恋》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陈晓光为之作序。陈晓光笔名晓光,著名词作家、诗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代表作有《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江山》《我像雪花天上来》等。曾任《词刊》主编,《中国艺术报》总编辑,中国音协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现将序言刊发,以飨读者。
我和郭华相识于1985年初春,我们一起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日本。那次的东瀛之旅是对1983年中日青年大联欢,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的回访。100名团员基本上是各省、市、区共青团和青联的领导人,个个风华正茂,英姿勃发。团长是胡锦涛同志,副团长是李克强同志;施光南、殷秀梅和我等文艺界的全国青联委员也跻身其中。出发前集中培训时,让我指挥大家练唱了几首歌曲。散会后唯一指出我打拍子不够精准的就是郭华,看得出来他是个酷爱文学艺术的“文青”。那时他已是河北团省委的领导,刚刚年满30岁,我们都还年轻。3年之后,听说他到我的祖籍河北省景县任职,先后担任县长、县委书记。30多年来我们偶有来往,君子之交,清清淡淡几十年。
郭华的主要工作经历,集中在衡水和与之相邻的沧州两个地区。这本书中开头一辑的十几篇作品,全部写的是衡水和沧州。他对两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人物故事、前世今生,如数家珍。《平原的传奇》一文,用优美的散文语言,叙述了衡水五千年的历史,既凝炼又厚重,既有思考又有故事,将衡水这个平原地区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顿生崇敬之心,陡增热爱之情。《林冲与沧州》一文,以可信的史实澄清了民间关于林冲与沧州的种种传说,讲述了历史上真实的沧州。他把衡水和沧州都视为自己的家乡,这了如指掌的熟悉和倾情讴歌的背后,是对家乡一言难尽的热爱,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不仅仅是《林冲与沧州》一文,他在好几篇文章中不厌其烦地重申:沧州不是发配之地。挚爱之情,充满字里行间。郭华自己说,这本书之所以定书名为《依恋》,就是因为对衡水和沧州这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沟槽村,1949年回过一次老家景县。由于战乱,近亲皆无,所以至今是唯一的一次,那年我才1岁。对于祖籍的情与景,人与事,旧日的贫穷灾难,艰难困苦,乃至沧州的狮子、景州的塔都是听老一辈人念叨的。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则是听郭华或衡水的老乡们逢年过节来京联谊时讲述的。记得郭华在衡水市任市委副书记时,我曾带领一批著名艺术家到“老、少、边、穷”地区“三下乡”演出,衡水便是其中一站。两天时间,我略微见识了故乡的风土人情。5年前,我又应邀和作曲家印青一起到衡水采风、参观了一天,回来创作了一首歌曲《衡水湖》。两次到衡水都是行色匆匆,走马观花,对家乡的了解和情感,比较起郭华来差了许多,为此惭愧郁郁在心。
浓厚的感情色彩,是郭华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衡水、沧州历史上都曾经是中国北方著名的贫困地区。写到昔日的贫困,能清晰感受到他笔触的沉重,写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他欣喜的情绪令人感同身受。对于亲人,他真挚的感情更是催人泪下。在《有关母亲的醒悟》一文中,写到母亲去世后的思念之情:“我多希望世上真的有鬼魂啊。如果有一天我一进房间看到娘在那儿,不仅不会害怕,还会毫不迟疑地上前抱住娘,大声问:娘,这么多日子,您撂下我们去哪儿了?!”不仅对家乡、对亲人,包括谈到工作的时候,也都感情满满。比如在谈脱贫攻坚的文章中,他说:“一次,和一位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聊天,我问:当年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你们都和老百姓讲什么呢?老同志告诉我,当时讲的话多了,哪里都记得,但有一句话,凡是在老区工作过的共产党人,肯定都对老百姓说过:‘等共产党坐了天下,一定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老同志的这句话,一直在我心头沉甸甸的,因为这是我们对老区人民的庄严承诺。”
郭华的文章语言流畅,不论写人、写事、抒情、讲理,总是娓娓道来,读起来没有生涩的感觉,特别是他善于用优美的散文语言来叙述历史。诸如《迁徙的家园》《九河之间》《武强文亦强》《靠海而兴》这些文章,以“讲史”为主,大量引用史料,但读起来丝毫不感到枯燥。他还尝试着从新的流行语言中汲取营养,比如在《闲读偶记两则》中,谈到正太铁路和阎锡山的关系时,他写到:“1902年工部侍郎盛宣怀同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修筑正太铁路的合同时,19岁的阎锡山还是太原一个准备报考武备学堂的小店员。对于修筑正太铁路他顶多是一个‘吃瓜群众’,别说干预整条铁路建设,恐怕连正太铁路的一根枕木也插不上手。”“吃瓜群众”就是近年来的网络语言,用在这里很贴切。他的文章中没有自己硬造出来、谁也看不懂的语言。在《林冲与沧州》一文的开头和结尾,他分别写到:“茅台因美酒而知名,普洱因好茶而知名,安庆因太平军与清军一战而知名,瑞金因中华苏维埃的‘红都’而知名……唯有沧州,因‘发配’而知名。而这‘发配’的来源,便是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林教头刺配沧州道’。”“对于林冲,他们宁可信其有。因为在他们的感情中,林冲早已成为熟人、朋友、甚至同乡。今天,他们仍然愿意让他作为家乡的一颗星,闪烁在新沧州的天幕上。”语言生动,回味无穷。
郭华的文章善于讲故事。就连《独特的力量》这样杂文体裁的文章,开头就是故事:“民国时期,天津一个金姓商人,特别信任知名中医施今墨。某次这位商人得病,恰巧施今墨不在天津,只得请了另外一名医生看病。但商人吃了这位医生的药,总觉得没有明显效果。后来听说施今墨回来了,赶紧请来。施今墨极为细心地把了脉,审视了处方,认为诊断正确,处方完全对症。可商人说什么不相信:倘若对症,怎么治不好病呢!施今墨无奈只得重新开了方子,结果商人依照施今墨的处方,吃了两剂药就好了,自然十分感谢。施今墨说:前面那位大夫的方子的确没错。中药都有别名,我只不过用药材的别名重新抄了一下他的方子。”这些生动的故事让他的文章愈加引人入胜。在《窦尔敦和他的故乡献县》一文中,他记叙了一个和窦尔敦同为献县人的纪晓岚的故事:“当年,纪晓岚回家探亲,驿卒抬其过献县单桥,一不小心跌了一跤,轿子摔倒在地,居然把纪晓岚从轿子里摔了出来。闯了如此大祸,轿夫吓得手足无措。不料想纪晓岚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土,随口吟道:‘忍饥已几日?疲癃不汝嗔。跌倒寻常事,我是故乡人。’驿卒虽然吃皇粮,但待遇非常之低,常常吃不上饭。连饭都吃不饱,能不疲惫吗?纪晓岚不仅体谅这些乡亲的苦处,还安慰他们:摔个跤算什么,不用怕,我也是献县老乡。”这个在有关纪晓岚的影视作品中从未被提及过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以幽默诙谐著称的一代文宗性格中的另一面,体现了他在家乡、在乡亲面前平和、亲切、随意的风度。张国立若早日读过郭华的这篇散文,编导《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连续剧时,就不会留下遗珠之憾了。
书中有一辑是“言论”。大概和郭华长期在基层工作有关系,这些言论文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接地气,紧密联系基层工作的实际,又有很强的理论深度,比如《力戒形式主义的“痕迹管理”》一文,在《人民日报》刊登之后,不仅被中宣部的“学习强国”平台选用,而且很快被收录到《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干部读本之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有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郭华就这“四心”所写的体会文章,《经济日报》专门开辟《增强“四心”,英勇战“疫”》专栏予以连续刊发。即使这一类的言论文章,郭华也力求写得生动流畅,比如《力戒形式主义的“痕迹管理”》一文,他这样切入:“‘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今天,走进兰考,遍地的泡桐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而兰考人把泡桐叫作‘焦桐’,因为这是当年焦裕禄同志带领他们栽种的。虽然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不到两年时间,但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改变面貌的痕迹永远留在了兰考大地上、兰考人民心里。”
书中那些写地方文化、寻根问祖的文章也非常受读者欢迎,诸如《平原的传奇》《林冲与沧州》在各种新媒体的浏览量超过百万人次,得益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作为一个衡水人,那些写衡水的文章,同样引起我对故乡的思念和无尽的联想。
40年来,郭华从农村青年倔强地成长为一名省级领导干部,其中的艰辛坎坷可想而知。在我的印象中郭华的口才好,文才亦好。虽然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但让人高兴的是,这本集子竟不是他大会小会上讲话的汇编,是名副其实个人写作的文集。无论散文、杂文、议论文,他都把对文学性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他用自己的语言传承历史,揭示哲理,讲述故事,抒发感情,实在难能可贵。
1972年天津市恢复创办了《天津文艺》杂志,在试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郭华的处女作小小说《账》,那一年他还是一个18岁的青年农民。从那时候开始,他便执著于业余写作。如今郭华退休了,如他自己所说:当了一辈子业余作者,现在终于成了专业作者。
文章千古事。人生能留下几本书,是大事也是好事。愿已经成为“专业作者”的郭华同志,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是为序。
2020年5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