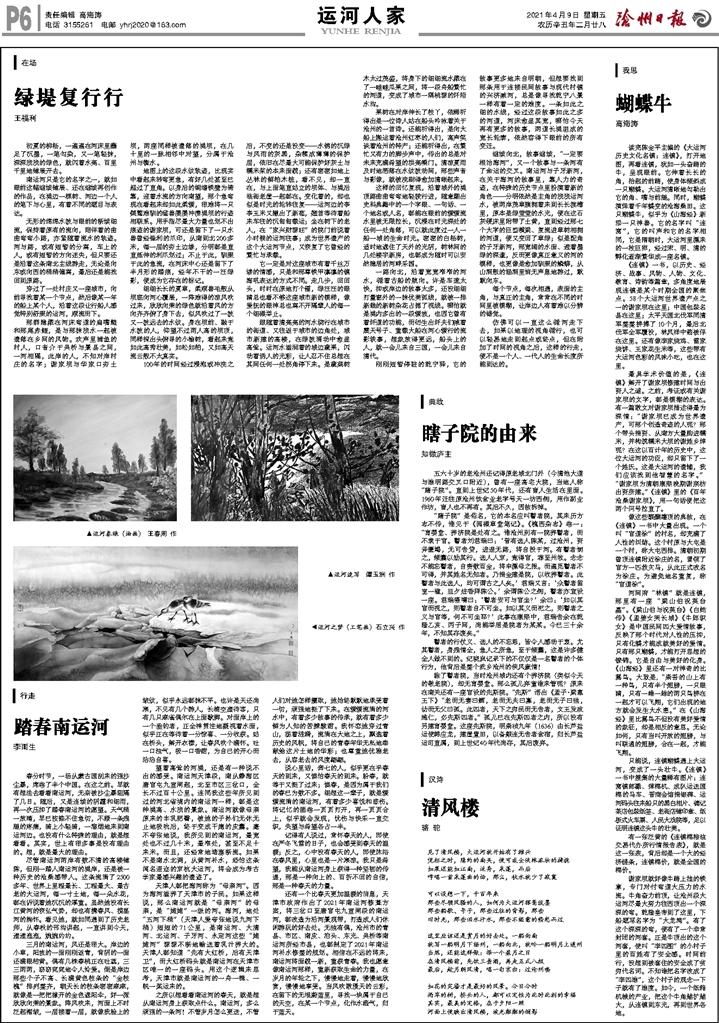初夏的柳杨,一遍遍在河床里蘸足了沉墨,一笔勾染,又一笔轻抹,深深浅浅的绿色,就闪着水亮、百里千里地铺展开去。
南运河只是它的名字之一,就如眼前这幅继续铺展、还在继续再创作的作品,在堤边一棵树、河边一个人的笔下与心里,有着不同的题目与表达。
无形的绵绵水波与眼前的断续细流,保持着原有的流向,陪伴着的曲曲弯弯小路,亦紧随着流水的轨迹。河与路,或有短暂的分离,车上的人,或有短暂的方向迷失,但只要还是沿着这条南北主线游走,无论是向东或向西的稍稍偏离,最后还是能找回到原路。
穿过了一处村庄又一座城市,向前寻找着某一个节点,然后像某一年的船上某个人,沿着这段让行船人感觉特别舒服的运河,顺流而下。
那群隐藏在河床弯道的扁嘴鲢和那尾赤鲤,是与那抹浅水一起被遗落在乡间的风物。欢声里捕鱼的村人,口音介于吴桥与景县之间,一河相隔,此岸的人,不知对岸村庄的名字;谢家坝与华家口夯土坝,两座同样被遗落的堤坝,在几十里的一脉相邻中对望,分属于沧州与衡水。
地图上的这段水纹轨迹,比现实中看起来转弯更急,有好几处甚至已超过了直角。以身后的铜墙铁壁为倚靠,迎着水流的方向南望,那个急弯现在看起来却如此柔缓,很难将一只桀骜难驯的猛兽屡屡冲溃堤坝的行迹相联系。用手指尽最大力量也划不出痕迹的谢家坝,可还是留下了一只水兽曾经锋利的爪印,从南到北200多米,每一层的夯土边缘,分明都是直直延伸的利爪划过;不止于此,驯服于此的急流,在河床中心还是留下了半月形的踏痕,经年不干的一汪绿影,便成为它存在的标记。
细细长长的夏草,柔顺兽毛般从坝底向河心覆展,一阵难得的凉风吹过来,欣欣向荣的绿色就沿着风的方向齐齐俯了身下去,似风吹过了一波又一波远去的水纹。身在坝前、融于水波的人,仰望不过两人高的坝顶,同样探出头俯寻的小榆树,看起来竟如此高秀壮美,如松如柏,又如高天流云般不太真实。
100年的时间经过浸泡或冲洗之后,不变的还是没变——水锈的沉绿与风雨的灰黑,杂糅成薄薄的保护层,依旧在尽最大可能保护好灰土与糯米浆的本来面貌;还有密密如地上丛林的鲜柏木桩,看不见,却一直在,与上面笔直站立的坝体、与堤后临街老屋一起都在。变化着的,却也似是时光的轮转往复——运河边的亭亭玉米又撇出了新苞,翘首等待着船来车往的沉甸甸载运;坐在树下的老人,在“家兴财源旺”的院门前说着小时候的运河往事;成为世界遗产的这个大运河节点,又恢复了它曾经的繁忙与承载。
它一定是对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只是和那尊铁甲凛凛的镇海吼表达的方式不同。走几步,回回头,时时在原地打个圈,绿汪汪的眼睛总也看不够这座城市新的模样,像爱抚的眼神总也离不开隔辈人的每一个细微举止。
跟随着清亮亮的河水绕行在城市的街道、又往返于城市的边角处,城市新建的高楼,在绿波涌动中愈显高耸。运河水滋润着的城边蔬果,闪动着诱人的光彩,让人忍不住总想在其间任何一处拐角停下来。是蔬菜树木太过茂盛,将身下的细细流水藏在了一畦畦瓜果之间,将一段舟船繁忙的河道,变成了城市一隅桃源的阡陌水沟。
果树在对岸伸长了枝丫,依稀听得出是一位诗人站在船头吟咏着关于沧州的一首诗。还能听得出,是向大船上搬运着沧州红枣的人们,高声笑谈着沧州的特产;还能听得出,在繁忙又有力的脚步声中,传出的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洪亮嗓门。清凉夏雨及时地洒落在水纹波动间,那些声音与影像,就被洗刷得愈加清晰起来。
这样的回忆复现,沿着城外的堤顶路曲曲弯弯地轻驶行进,随意翻出史料典籍中的一个字眼、一句话、一个地名或人名,都能在眼前的缓缓流水里被无限拉长,沉浸在时光深处的任何一处角落,可以就此度过一人一船一城的生命时光。密密的白杨树,适时地遮住了天外的光阴,树林间的几处楼宇新房,也都成为随时可以安然隐居的河畔乐园。
一路向北,沿着宽宽窄窄的河水,循着古船的航向。许是车速太快,抑或岸边的故事太多,还没细细打量窗外的一抹优美弧线,就被一排新栽的新树杂花占据了视线。哪怕就是堤内多出的一段缓坡,也因它曾有着纤道的功能,而衍生出纤夫们喊着震天号子、重载大船在河心缓行的流影轶事,想象放得更远,船头上的人,就一会儿来自三国,一会儿来自清代。
刚刚短暂停驻的乾宁驿,它的故事更多地来自明朝,但想要找到那条用于连接民间故事与现代村镇的兴济减河,总是像寻找乾宁八景一样有着一定的难度。一条如此之细的水线,经过这段故事如此之多的河道,河床愈显其宽,哪怕今天再有更多的故事,两道长堤组成的宽长轮廓,依然容得下眼前的所有变迁。
继续向北,故事继续,“一定要根治海河”,又一个故事与一条河有了命运的交叉。南运河与子牙新河,在关于海河的故事里,靠人力的奇迹,在特殊的历史节点里扮演着新的角色——分明依然是主角的浅浅运河水,被两岸茂草簇拥着来到长长渡槽里,原本是绿莹莹的水光,便在这石灰硬床里附带了土黄,直到经过那七个大字的巨型横梁、复流进草树相拥的河道,便又变回了草绿;似是配角的子牙新河,那宽阔的水面、透着墨绿的深邃,反而更像真正意义的河的模样,也更像是愈加驯服的鳞蟒,从山洞般的涵洞里悄无声息地游过,默默向东。
每个节点,每次相遇,表面的主角,与真正的主角,常常在不同的时间里被模糊,让岸边人有着难以分辨的错觉。
仿佛可以一直这么循河走下去,如果以地理的视角循行,也可以轻易地走到起点或终点,但在附加了时间的视角之后,这样的行走,便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生命长度所能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