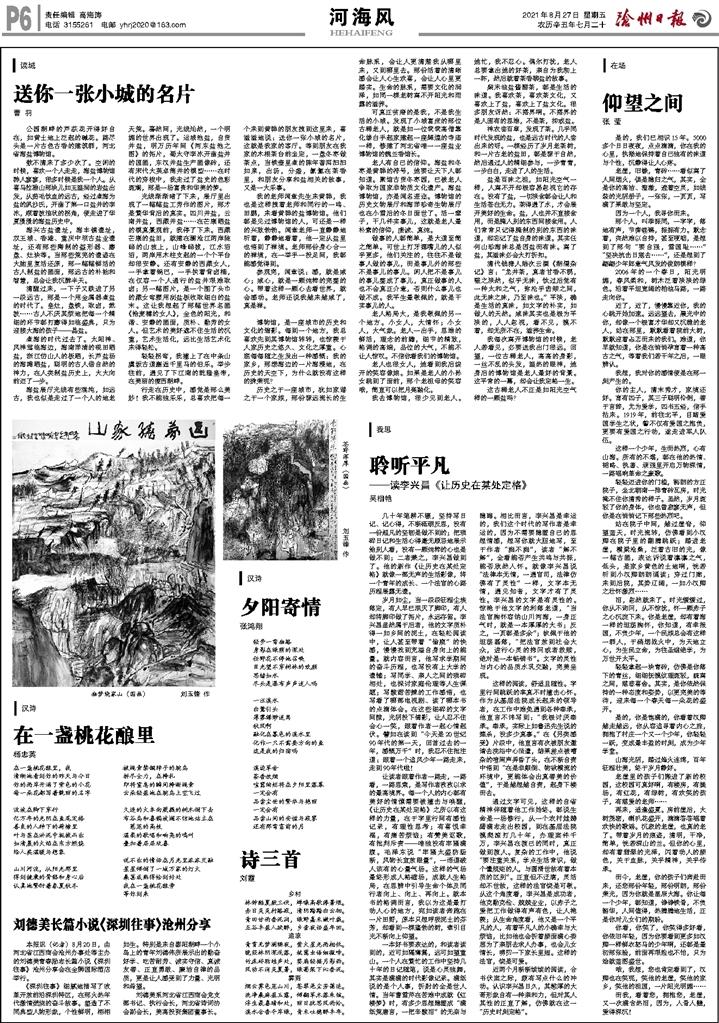公园湖畔的芦荻花开得好自在,如黄土地上泛起的碱花。路尽头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河北省海盐博物馆。
数不清来了多少次了。空闲的时候,喜欢一个人走走,海盐博物馆游人寥寥,很多时候是我一个人。从喜马拉雅山那块儿如玉温润的岩盐出发,从茹毛饮血的远古,经过煮海为盐的夙沙氏,开凿了第一口盐井的李冰,顺着波浪状的拐角,便走进了华夏漫漫的海盐历史中。
海兴古盐遗址,海丰镇遗址,双王城、香港、重庆中坝古盐业遗址,还有那些陶制的盔形器、磨盘、灶块等。当那些荒芜的遗迹在大脑里复活还原,那一幅幅鲜活的古人制盐的画面,那远古的朴拙和智慧,总会让我沉醉半天。
清醒过来,一下子又跌进了另一段远古,那是一个用金属器煮盐的时代了。垒灶,盘铁,取卤,熬波……古人不厌其烦地把每一个精细的环节都打磨得如临盛典,只为迎接大海的孩子——晶盐。
煮海的时代过去了。太阳神、风神驾临海边,海南洋浦的砚田晒盐,浙江岱山人的板晒,长芦盐场的海滩晒盐,聪明的古人借自然的神力,在人类制盐历史上,大大向前迈了一步。
海盐展厅光线有些混沌,如远古,我也似是走过了一个人的地老天荒。蓦然间,光线灿然,一个明媚的世界出现了。运城池盐,自贡井盐,明万历年间《河东盐池之图》的拓片,蜀太守李冰开凿盐井的国画,东汉井盐生产画像砖,还有宋代大英卓筒井的模型……在时代的穿梭中,我走过了盐史的色彩斑斓,那是一场富贵和华美的梦。
光线渐渐暗了下来,展厅里出现了一幅幅盐工劳作的图片,那才是繁华背后的真实。四川井盐,云南井盐,西藏井盐……在芒康晒盐的模真景观前,我停了下来。西藏芒康的盐田,就建在澜沧江两岸陡峭的山坡上,山峰峭拔,江水滔滔,两岸用木柱支起的一个个平台却很安静。还有安静的西藏女人,一手拿着锅巴,一手扶着背卤桶,在仅容一个人通行的盐井艰难取卤;另一幅图片,是一个围了头巾的藏女弯腰用刮盐板收取细白的盐末。这让我想起了那幅世界名画《拾麦穗的女人》,金色的阳光,和谐、安静的画面,质朴、勤劳的女人。但艺术的美好遮不住生活的沉重,艺术生活化,远比生活艺术化来得轻松。
轻轻拐弯,我撞上了在中条山虞坂古道邂逅千里马的伯乐。举步往前,遇见了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在美丽的瘦西湖畔。
行走在历史中,感觉是那么美妙!我不能独乐乐,总喜欢把每一个来到黄骅的朋友拽到这里来,喜滋滋地说:送你一张小城的名片,这就是我家的客厅。等到朋友在我家的木根茶台前坐定,一盘冬枣做茶点,当铁壶里煮的陈年普洱汩汩如泉,出汤,分盏,氤氲在茶香里,和朋友分享和盐相关的故事,又是一大乐事。
我的老师闻章先生来黄骅,我也是这样拽着老师和同行的一鸣、田鹏,来看黄骅的盐博物馆。他们都是见过博物馆的人,可还是一样的兴致勃勃。闻章老师一直静静地听着,静静地看着,他一定从盐里也悟到了禅境。老师那份身心合一的禅境,在一举手一投足间,我都能感觉得到。
参观完,闻章说:感,就是咸心;咸心,就是一颗纯粹的完整的心。带着这样一颗心去看世界,就会感动。老师还说我越来越咸了,真是禅。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缩影。每到一个地方,我总喜欢先到其博物馆转转,也惊羡于人家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厚重。心底每每随之生发出一种感慨:我的家乡,那渤海边的一片海浸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殊荣呢?
历史之于一座城市,犹如家谱之于一个家族,那份源远流长的生命脉系,会让人更清楚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那份活着的清晰感会让人心生欢喜,会让人心里更踏实。生命的脉系,需要文化的润泽,如同一棵老树离不开阳光和雨露的滋养。
可真正贫瘠的是我,不是我生活的小城。发现了小城富庶的那位古稀老人,就是如一位茕茕高僧靠化缘白手起家建起一座辉煌的寺庙一样,修建了河北省唯一一座盐业博物馆的魏兰香馆长。
老人有自己的信仰。海盐和冬枣是黄骅的符号,她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聚馆古贡冬枣园,已被老人争取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海盐博物馆,亦是闻名遐迩。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展厅和海洋珍奇生物展厅也在小雪后的冬日面世了。活一辈子,干几件实事儿,这就是老人最朴素的信仰,虔诚、真纯。
做事的人都简单,是大道至简之简单。可世上打牙撂嘴儿的人似乎更多,他们关注的,往往不是做事人做的事儿,而是事儿外的那些不是事儿的事儿。闲人把不是事儿的事儿整成了事儿,真正做事的人也不会真正介意,否则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我平生最敬佩的,就是干实事儿的人。
老人格局大,是我敬佩的另一个地方。小女人,大情怀;小女人,大气象。老人一出手,思维的鲜活,理念的前瞻,细节的精致,格调的高端,品位的大气,不能不让人惊叹。不信你看我们的博物馆。
老人也很女人,她看到我后绽开的笑容像娘。如果是老人的小孙女跳到了面前,那个老祖母的笑容哦,简直可以把月亮融化。
我去博物馆,很少见到老人。她忙,我不忍心。偶尔打扰,老人总要拿出她的好茶,亲自为我沏上一杯,然后就着茶香聊盐的故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生活的味道。我喜欢茶,喜欢茶文化,又喜欢上了盐,喜欢上了盐文化。很多朋友讶然:不搭界啊。不搭界的是人固有的思维,不是茶,抑或盐。
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几乎同时代发现的盐,也是远古时代的人尝出来的呀。一棵经历了岁月老茶树,和一片古老的盐田,都是源于自然,然后通过人的精细参与,一步青青,一步白白,走进了人的生活。
盐是百味之祖,如阳光空气一样,人离不开却极容易忽视它的存在。没有了盐,一切淡食都会让人和生活苍白无力。茶得遇了水,才会展开美好的生命。盐,人也并不直接食用,而是腌入别的东西间接食用。人们常常只记得腌制的别的东西的味道,却忘记了盐自身的味道。其实任何山珍海味总是因盐而有味。离了盐,其滋味必会大打折扣。
清代钱塘人陆次云撰《湖儒杂记》言:“龙井茶,真者甘香不洌,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平淡,确是生活的真味,如文字的朴实,如做人的天然。咸味其实也是极为平淡的,人人忽视,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滋养生命。
我每次离开博物馆的时候,老人若看见,必要送我出门很远。回望,一位古稀老人,高高的身影,一丝不乱的头发,温热的眼神,她身后的博物馆是老人最好的背景。这平常的一幕,却会让我定格一生。
这古稀老人不正是如阳光空气样的一颗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