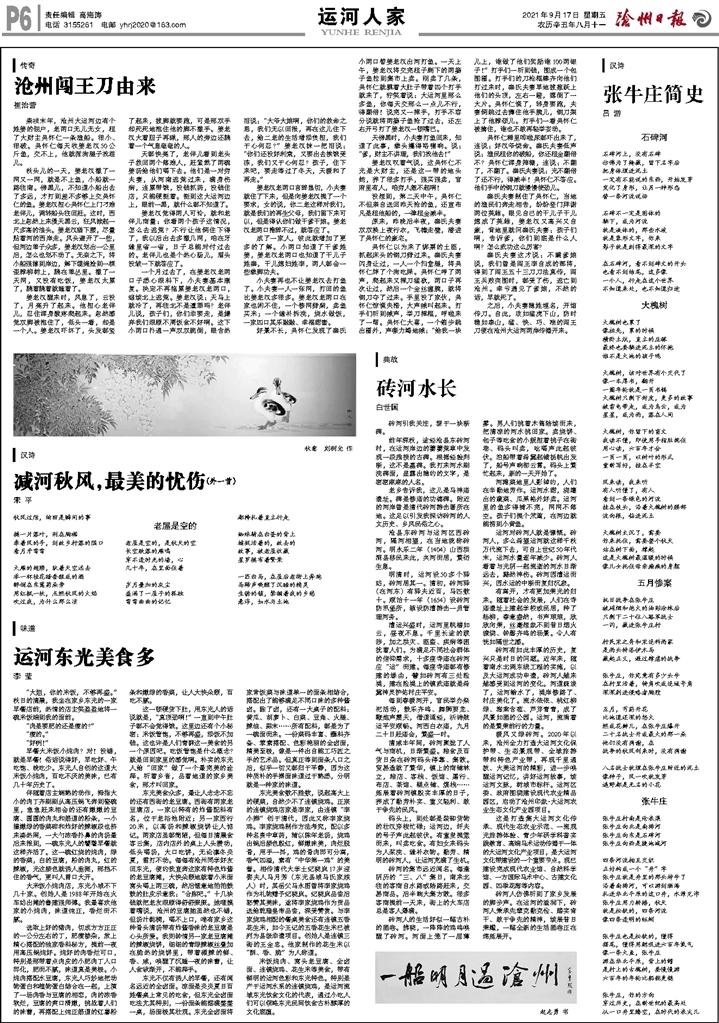白世国
砖河引我关注,源于一块断碑。
前年深秋,途经沧县东砖河村,在运河岸边的萋萋荒草中发现一段残损的古碑。根据经验判断,这不是墓碑。我打来河水刷洗碑面,显露出隐约的文字,是密密麻麻的人名。
老乡告诉我,这儿是马神庙遗址。碑是修庙的功德碑。附近的河岸曾是清代砖河游击署所在地。这足以引发我探访砖河的人文历史、乡风民俗之心。
沧县东砖河与运河区西砖河,隔河相望,在当地统称砖河。明永乐二年(1404)山西洪洞县移民来此,夹河而居,繁衍生息。
明清时,运河设50多个驿站,砖河居其一。清初,砖河驿(在河东)有驿夫近百,马匹数十。顺治十一年(1654)设砖河防汛堡所,额设防漕游击一员管理河务。
漕运兴盛时,运河里帆樯如云,昼夜不息。千里长途的跋涉,加之洪灾、匪盗、疾病等困扰着人们。为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信仰需求,十多座寺庙在砖河应“运”而建。每座寺庙都有修建的缘由,譬如砖河有三处险堤,建在险堤上的镇武庙就是希冀神灵护佑村庄平安。
每到春暖河开,官民举办祭祀活动,鼓乐齐鸣、舞狮耍龙、鞭炮声震天,僧道诵经,祈祷航运平安顺畅。河西白衣庙,九月二十日赶庙会,繁盛一时。
清咸丰年间,砖河聚拢了人气与商机,日渐繁盛。粮食及百货日杂在砖河码头停靠、集散。贸易造就了繁华,镇上的商铺林立,粮店、客栈、饭馆、屠行、布店、茶馆、糕点铺、煤栈……延展着砖河镇殷实丰厚的日子,养成了勤劳朴实、重义轻利、敢于争先的民风。
码头上,到处都是装卸货物的壮汉穿梭忙碌;运河边,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有童叟提篮而来,叫卖吃食。有妇女来码头为人浆洗、缝补衣物。勤劳、精明的砖河人,让运河充满了生机。
砖河的集市远近闻名。每逢阴历的“三、八”集日,南来北往的客商自水路或陆路赶来,交易商品。后半晌大集方散。很多客商提前一天来,街上的大车店总是客人爆满。
砖河人的生活好似一幅古朴的画卷。拂晓,一阵阵的鸡鸣唤醒了砖河。河面上笼了一层薄雾。男人们挑着木筲陆续而来,把清凉的河水挑回家。卖烧饼、包子等吃食的小贩担着挑子在街巷、码头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泊船带着希冀起锚扬帆出发了,船号声响彻云霄。码头上繁忙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河滩菜地里人影绰约,人们在辛勤地劳作。运河水甜,浇灌出的蔬菜、瓜果格外好卖。运河里的鱼多得捕不完,网网不落空。孩子们提个笊篱,在河边就能捞到小黄鱼。
运河对砖河人就是慷慨。砖河人,多么希望运河就这样千秋万代流下去,可自上世纪50年代末,运河水量逐年减少。砖河人看着与光阴一起流逝的河水日渐远去,黯然神伤。砖河因漕运而兴,因水运的中断而复归沉寂。
有离开,才有更加荣光的归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寺庙遗址上建起学校或民居,种了杨柳,春意盎然,书声琅琅,欣欣向荣,丝毫想象不到昔日烟火缭绕、钟磬齐鸣的场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砖河有如此丰厚的历史,复兴只是时日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以及大运河成功申遗,砖河人越来越感受到运河的变化。河道疏浚了,运河输水了,堤岸修路了、村庄美化了。流水依依、桃红柳绿、海棠含苞、芦芽青青,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运河,流淌着的是繁荣前行的力量。
暖风又绿砖河。2020年以来,沧州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保护带、生态景观带、全域旅游带和特色产业带,再现千里通波、大美运河的精彩,进一步唤醒运河记忆,讲好运河故事,续运河文脉,树城市标杆。运河区委、政府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精品园区,启动了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
这是打造集大运河文化传承、现代生态农业示范、一流观光旅游体验、青少年研学科普实践教育、高端马术运动传播于一体的大运河文化产业项目,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现已建设完成现代农业馆、自然科学馆、一方国际马术中心、古建文化园、四季花海等内容。
砖河人仿佛听到了家乡发展的脚步声。在运河的滋润下,砖河人秉承先辈克勤克俭、踏实肯干、敢于争先的精神,续展昔日荣耀,一幅全新的生活画卷正在绵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