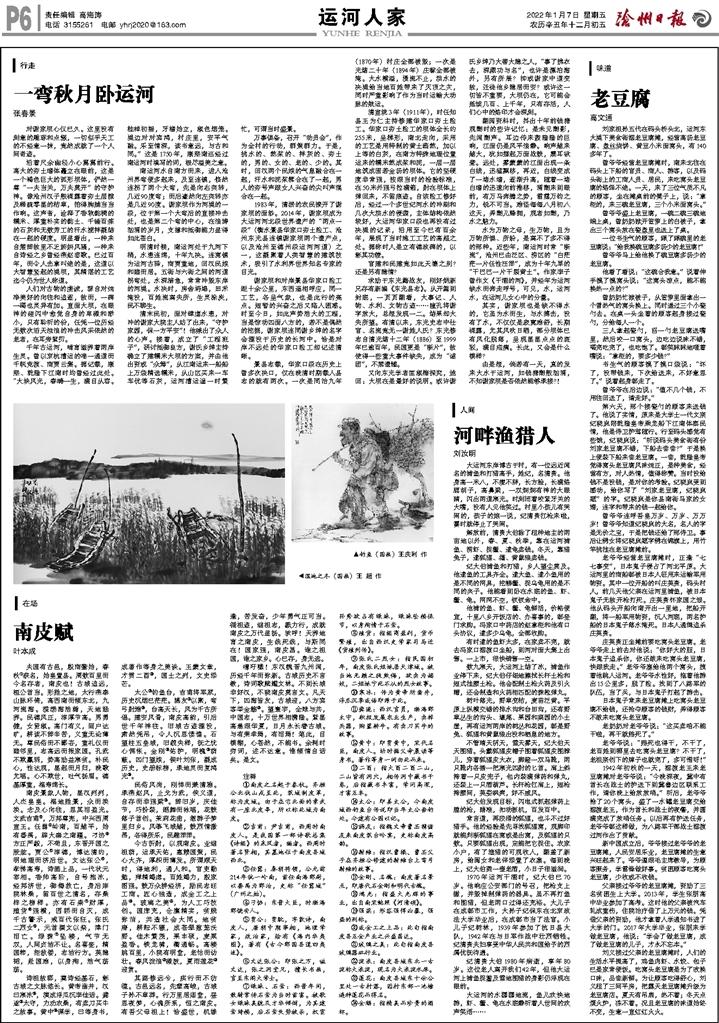对谢家坝心仪已久。这里没有刻意的雕琢和点缀,一切似乎天工的不经意一抹,竟然成就了一个人间奇迹。
沿着尺余幽径小心翼翼前行。高大的夯土墙体矗立在眼前,这是一个褐色巨大的弧形坝体,俨然一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守护神。像沧州汉子般裸露着夯土层隙及稀疏零星的枯草,拍得胸脯当当作响。这声音,诠释了香软黏稠的糯米、厚重朴实的黏土、千锤百炼的石灰和无数劳工的汗水搅拌凝结在一起的硬度。明显看出,一种来自楚辞故里不乏娇妍风骚,一种来自诗经之乡曾经燕赵悲歌。已过百年,而令人击掌叫绝的是,这道以大智慧竖起的堤坝,其精湛的工艺迄今仍为世人称道。
人们对古物的虔诚,源自对纯净美好的向往和追逐,故而,一碑一碣也灵异有加。直面大坝,在眼神的碰闪中愈觉自身的卑微和渺小,只有聆听的份,任凭一位历经无数次滔天浊浪的冲击风采依然的老者,在耳旁絮叨。
千年古运河,哺育滋养着两岸生灵。曾以京杭漕运的唯一通道而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据记载,康熙、乾隆下江南时均曾经过此处。“大块风光,春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始立,淑色烟笼。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融。乐至情深,读书意远,与古和同。”这是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南运河时填写的词,极尽溢美之意。
南运河水自南方而来,进入沧州界弯便多起来,及至连镇,倏然连拐了两个大弯,先是向右突转,几近90度弯;而后遽然向左突转亦是几近90度。谢家坝作为河堤的一段,位于第一个大弯后的直接冲击处,也是第二个弯的中心,在浪涛汹涌的岁月,支撑和抵御能力显得如此苍白。
明清时候,南运河处于九河下梢,水患连绵,十年九决。连窝镇为运河古驿,商贾重地,回汉民族和睦而居。五街与六街之间的河道拐弯处,水深湍急,常常冲毁东岸的河堤。水决时,房舍坍塌,田禾淹没,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清末民初,面对肆虐水患,对冲的谢家大院主人站了出来,“守护家园,保一方平安”!他喊出了众人的心声。接着,成立了“工程班子”,研讨抵御良方,谢氏乡绅主持确立了建糯米大坝的方案,并由他出资或“众筹”,从江南运来一船船上万袋精选糯米,从山区买来一车车优等石灰,运河漕运逞一时繁忙,可谓当时盛景。
万事俱备,召开“动员会”,作为全村的行动,群策群力。于是,挑水的、熬浆的、拌灰的、夯土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其时,回汉两个民族的气息融合在一起,汗水和泥浆糅合在了一起,男人的夯号声跟女人兴奋的尖叫声混合在一起。
1983年,清淤的农民撩开了谢家坝的面纱。2014年,谢家坝成为大运河河北段世界遗产的“两点一段”(衡水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沧州东光县连镇谢家坝两个遗产点,以及沧州至德州段运河河道)之一,这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建筑技术,吸引了水利界世界知名专家的目光。
谢家坝和对岸景县华家口险工距十余公里,东西遥相呼应,同一工艺,各呈气象,也是此行的亮点。短暂的兴奋之后又陷入困惑。时至今日,如此声势浩大的工程,当是惊动四面八方的,若不是偶然的挖掘,谢家坝连同谢乡绅的名字会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恰是对岸不远处的华家口险工却记述清晰。
景县志载,华家口段在历史上曾多次决口,仅在晚清时期载入县志的就有两次。一次是同治九年(1870年)村庄全部被毁;一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庄稼全部被淹。大水横溢,漫流不止,洪水的决堤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同时严重影响了作为当时运输大动脉的航运。
清宣统3年(1911年),时任知县王为仁主持修建华家口夯土险工。华家口夯土险工的坝体全长约255米,呈梯形,南北走向,采用的工艺是用特制的黄土蒸熬,加以上等的白灰,在南方特殊地理位置运来的糯米熬成浆和泥,一层一层地筑成固若金汤的坝体。它的坚硬度非常强,按照当时的检验标准,在50米外强弓拉满箭,射在坝体上弹回来,不留痕迹。自该险工修好后,经过一个多世纪河水的冲刷和几次大洪水的侵袭,主体结构依然较好,大运河华家口段也再没有过决堤的记录,沿用至今已有百余年,展现了当时施工工艺的高超之处。据称时人是立有德政碑的,以彰其功绩。
官建和民建竟如此天壤之别?还是另有隐情?
求助于东光籍战友,刚好炳新兄存有新编《东光县志》。从开篇到封底,一页页翻看,大事记、人物、水利、文物古迹……瞳孔将谢字放大,总想发现一二。结果却大失所望。有清以来,东光史志中仕官、名流竟无一谢姓人氏?东光修志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至1999年已逾百年,民国更是“断片”,故使得一些重大事件缺失,成为“谜团”,不禁遗憾。
又向东光学者匡淑梅探究,她回:大坝在是最好的说明。或许谢氏乡绅乃大善大隐之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也许是漂泊海外,另有所展?抑或谢家中道变故,迁徙他乡隐居而安?或许这一切皆不重要,大坝仍在,它可能会延续几百、上千年,只有存活,人们心中的烙印才会深刻。
翻阅资料时,抖出十年前钱塘观潮时的些许记忆:是未见潮影,先闻潮声。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江面仍是风平浪静。响声越来越大,犹如擂起万面战鼓,震耳欲聋。远处,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一条白线,迅猛飘移,再近,白线变成了一堵水墙,逐渐升高,随着一堵白墙的迅速向前推移,涌潮来到眼前,有万马奔腾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锐不可当。难怪每每八月初八这天,弄潮儿蜂拥,观者如潮,乃水之魅力。
水为万物之母,生万物,且为万物所惧、所盼,是离不了多不得的那种。近些年,南运河时常“断流”,沧州已由泛区、涝区的“白茫茫一片任性汪洋”,成为十年九旱的“干巴巴一片干裂黄土”。作家李子曾作文《干涸的河》,并经年为运河缺水而奔走呼号,可见,水,运河水,在运河儿女心中的分量。
其实,谢家坝也是缺不得水的,它虽为水而生,与水搏击,没有了水,不仅仅是寂寞难舒,长期裸露,尤其风吹日晒,部分坝体已有风化脱落,呈现星星点点的斑驳,满目疮痍。长此,又会是什么模样?
由是想,倘若有一天,真的发来大水于运河,如钱塘潮般汹涌,不知谢家坝是否依然能够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