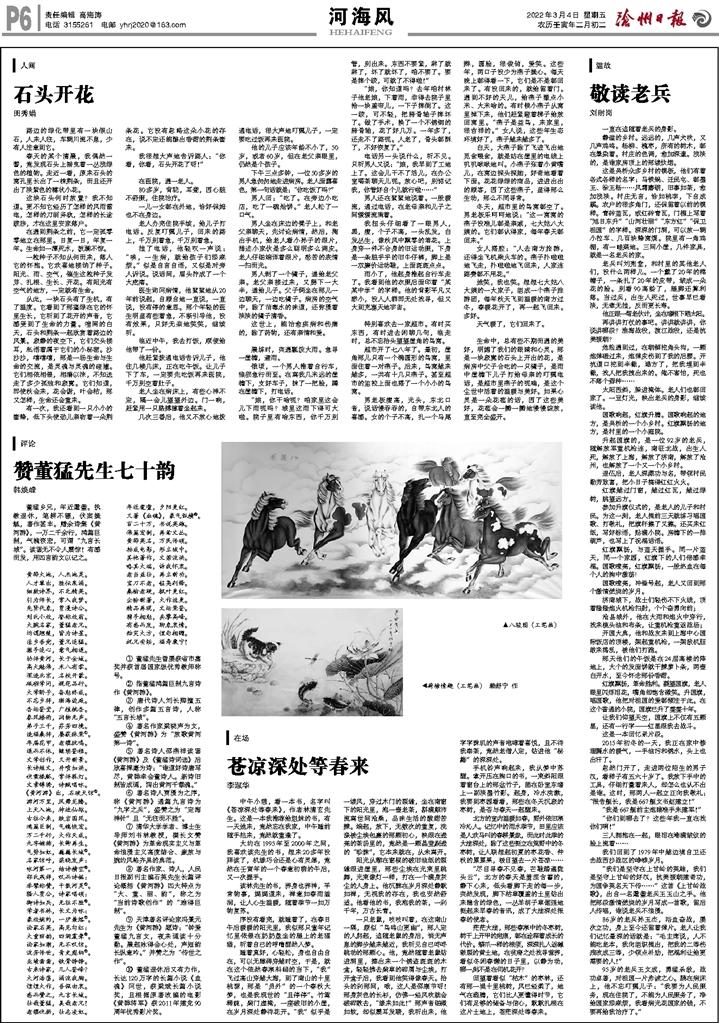一直在追随着老兵的身影。
静谧的乡村。远远的,几声犬吠,又几声鸡鸣。杨柳、槐枣,所有的树木,都在晕染着。村庄的色调,愈加深邃。浅淡的,是谁家房顶上的那缕炊烟。
这是吴桥众多乡村的模板,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名字:马铁锅、迁民屯、都墨王、徐王杨……风霜磨砺,旧事如茶,愈加浅淡。村庄无言,恰如桃李,下自成蹊。农户的很多角门,还保留着以前的模样。青砖蓝瓦,或红砖青瓦,门楣上写着“旭日东升”“山河壮丽”“东方红”“保卫祖国”的字样。深深的门洞,可以放一辆小拉车、几百块蜂窝煤。院里有一角鸡棚,有一畦菜地。三间小屋,几件家具,就是一名老兵的家。
老兵叫刘宪堂,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们,没什么两样儿。一个戴了20年的棉帽子,一条扎了20年的皮带,皱成一朵花的脸。别看90高龄了,腿脚还算利落。当过兵,出生入死过,世事早已看淡,无牵无挂,反而更长寿。
他正跟一帮老伙计,坐在墙根下晒太阳。
再讲讲打仗的事吧。讲讲就讲讲,你说讲哪段?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还是抗美援朝?
危险遇到过,在朝鲜挖角头沟,一颗炮弹砸过来,炮弹皮伤到了我的后腰。开坑道口挖到半截,塌方了,把我埋到半截,找人把我拽出来的。俺不害怕,死也不落个孬种……
太阳西斜,躲进掩体。老人们也都回家了。一豆灯光,映出老兵的身影,继续读他。
国歌响起,红旗升腾。国歌响起的地方,是吴桥的一个小乡村。红旗飘扬的地方,是村里的一个小庭院。
升起国旗的,是一位92岁的老兵,随解放军重机枪连,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济南,解放了沧州,也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小乡村。
退伍后,老人深藏功与名,带领村民勤劳致富,把小日子搞得红红火火。
红旗越过门窗,越过红瓦,越过绿树,眺望远方。
参加升旗仪式的,是老人的儿子和村民。为这一刻,老人提前三天就练习唱国歌、打敬礼,把旗杆擦了又擦。还买来红纸,写好标语,贴满小院。房檐下的一排葫芦,也写上了祝福话语。
红旗飘扬,与蓝天握手。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家园,红旗下的人们倍感幸福。国歌嘹亮,红旗飘扬,一股热血在每个人的胸中激荡!
国歌嘹亮,冲锋号起,老人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济南城下,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顶着隆隆炮火机枪扫射,个个奋勇向前;
沧县城外,他在大雨和炮火中穿行,找来梳头油和布条,让重机枪重返战场;
开国大典,他和战友来到上海中心国际饭店的顶楼,架起重机枪,一架敌机胆敢来捣乱,被他们打跑。
那天他们的午饭是在24层高楼的阵地上,大个的发面饼就干辣萝卜条,两壶白开水,至今怀念那份香甜。
红旗飘扬,革命胜利。凝望国旗,老人眼里闪烁泪花,嘴角却饱含微笑。升国旗,唱国歌,他把对祖国的爱都倾注于此。在这个普通的小院,国旗已升了整整十年。
让我们仰望天空,国旗上不仅有五颗星,还有一行字——红星照我去战斗。
这是一本回忆录片段。
2015年初冬的一天,我正在家中修理漏水的暖气,一手油污和锈水,头上也出汗了。
忽然门开了,走进两位陌生的男子汉,看样子有五六十岁了。我放下手中的工具,仔细打量着来人,却怎么也认不出是谁。这时,那两人一起立正向我敬礼:“报告艇长,我是667艇文书赵建立!”
“我是667艇前主炮瞄准手朱建军!”
“你们到哪去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啊!”
三人拥抱在一起,眼泪在堆满皱纹的脸上流着……
我们回到了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西沙战区的峥嵘岁月。
“我们是坚守在上甘岭的英雄,我们是坚守上甘岭的好汉,抗美援朝建奇功,为国争英名天下传……”这首《上甘岭战歌》,出自一名耄耋老兵王玉山之手。他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写成一首歌,留后人传唱,谁说老兵不浪漫。
86岁的老兵孙玉杰,浴血奋战,屡次立功,身上至今还留着弹片。老人让我们记忆最深的话就是:“毛主席说,人不能吃老本,我向组织提出,把我的二等伤残改成三等,少领点补助,把福利让给更需要的人!”
95岁的老兵王文成,勇猛杀敌,战功卓著,对祖国一片赤诚之心。躺在病床上,他不忘叮嘱儿子:“我要为人民服务,现在住院了,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净给国家添麻烦,我看病光花国家的钱,不要再给我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