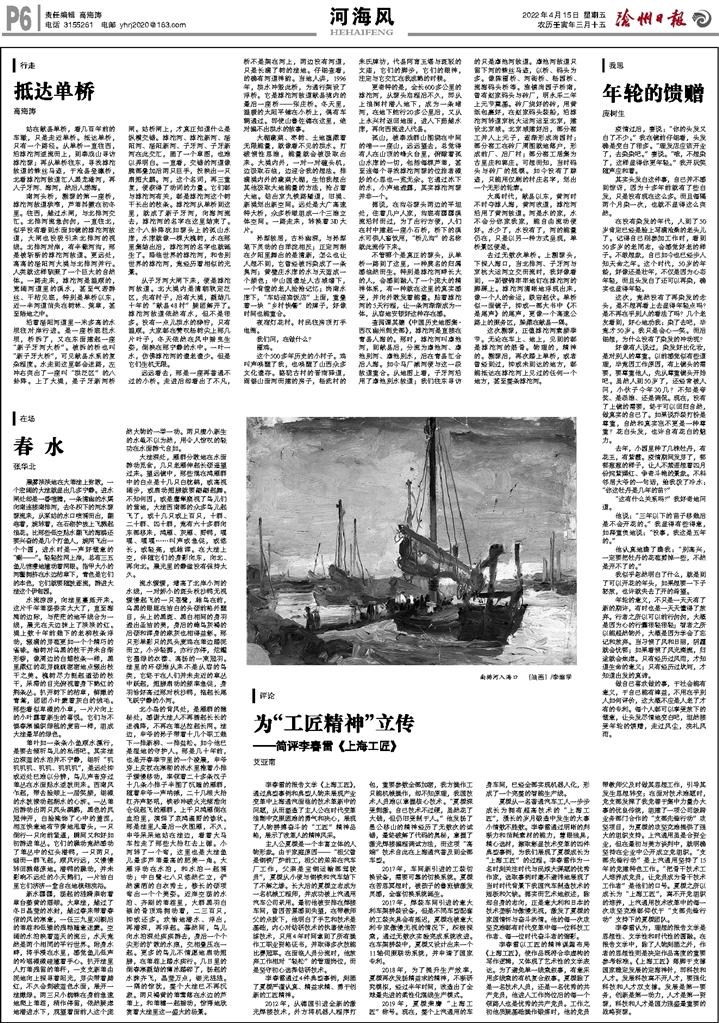站在献县单桥,看几百年前的车辙,只是走近单桥。抵达单桥,只有一个路径。从单桥一直往西,沿滹沱河逆流而上,到泰戏山寻访滹沱源;再从单桥往东,寻找滹沱故道的蛛丝马迹,于沧县登瀛桥,北看滹沱河故道汇入黑龙港河,再入子牙河、海河,然后入渤海。
南河头桥,溯源的第一座桥,滹沱河故道狭窄,芦苇抖擞在初冬里。往西,越过水闸,与北排河交汇。北排河流急匆匆,一直往北,似乎没有看到水面如镜的滹沱河故道,大闸也没吸引来北排河的视线。北排河对岸,有半截河沟,那是被斩断的滹沱河故道。更远处,高高的滏阳河大堤与北排河并行。人类就这样驯服了一个巨大的自然体。一路走来,滹沱河是温顺的,宽阔河道里的溪水,甚至气若游丝、干枯见底,特别是单桥以东,近一半河道消失在树林、荒草,甚至陆地之中。
沿着滏阳河道里一米多高的水坝往对岸行进。是一座桥底拦水坝,桥拆了,又在东面建起一座“新子牙河大桥”。被拆的桥也叫“新子牙大桥”,可见献县水系的复杂程度。水走到这里都会迷路,左冲右突出了一座叫“洪泛区”的八卦阵。上了大堤,是子牙新河桥闸。站桥闸上,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纵横交错。滹沱河、滹沱新河、滏阳河、滏阳新河、子牙河、子牙新河在此交汇,画了一个草图,也难以弄明白。一直看,交错的河道像腕部叠加后两只巨手,投映出一只扇翅大鹏。河,这个名词,再三重复,便获得了动词的力量。它们都与滹沱河有关,都是滹沱河这个树干长出的枝条。滹沱河从单桥到这里,就成了新子牙河,向海河流去,滹沱河的名字在这里结束了。这个八卦阵犹如源头上的孤山水库,水库就像一棵大槐树,水在那里集结出后,滹沱河的名字也就诞生了。降临世界的滹沱河,和告别世界的滹沱河,竟经历着相似的光景。
从子牙河大闸下来,便是滹沱河故道。北大堤内是清朝软定泛区,先有村子,后有大堤,凝结几十年的“献县48村”疑团解开了。滹沱河故道依然有水,但不是很多。没有一点儿洪水的狰狞,只有温顺。大家都在赞叹杨树尖上那几片叶子,冬天依然在风中摇曳生姿,倒映在那宁静的水中。一叶一水,仿佛滹沱河的遗老遗少。但是它们生机无限。
远远看去,那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小桥。走进后却看出了不凡,桥不是架在河上,两边没有河道,只是长满了树的洼地。仔细查看,的确有河道神韵。当地人讲,1996年,洪水冲毁此桥,为通行架设了浮桥。它是滹沱河故道献县境内的最后一座桥——张庄桥。冬天里,温暖的太阳平铺在小桥上,偶有车辆通过。即使山鲁佐德在这里,绝对编不出洪水的故事。
大棚蔬菜、枣树、土地蕴藏着无限能量,就像看不见的洪水。打破惯性思维,能量就会被汲取出来。大堤内外,一对一对磕头机,边汲取石油,边迎合我的想法。排满堤内外的蔬菜大棚,生怕我想出其他汲取大地能量的方法,抢占着大地。钻出京九铁路隧道,旧堤、新堤划出新空间。远处是大广高速特大桥,众多桥墩组成一个三维立体空间。一路走来,转换着3D大片。
孙犁故居,古朴幽深,与孙犁笔下灵动的白洋淀相反;正定河湖在夕阳里舞出的是清新,怎么也让人想不到,它曾经被污染成了一条臭河;黄壁庄水库的水与天蓝成一个颜色;中山国遗址人古城墙下,一个背筐的老人捡拾记忆;岗南水库下,“车站迎宾饭店”上面,重叠着一块“乡村快餐”的牌子,好像时间也能重合。
夜宿灯花村。村民往房顶打手电筒。
我们问,在做什么?
圈鸡。
这个500多年历史的小村子。鸡叫声唤醒了我,也唤醒了山西众多文化遗存。骆驼古村的晋商驿道,阎锡山面河而建的房子,杨武村的朱氏牌坊,代县阿育王塔与斑驳的文庙,它们的脚步,它们的眼神,注定与它交汇在我成熟的时候。
更奇特的是,全长600多公里的滹沱河,从源头启程后不久,即从上浪涧村潜入地下,成为一条暗河,在地下蛇行20多公里后,又从上永兴村返回地面,进入下茹越水库,再向西流进入代县。
孤山,被泰戏群山围绕在中间的唯一一座山,远远望去,总觉得有人在山顶的峰火台里,俯瞰着孤山水库的一切,包括每棵芦苇,甚至连每个寻找滹沱河源的位旅者微妙的心思也一览无余。它通过冰下的水,小声地透露,其实滹沱河源并非一个。
据说,在沟谷源头两边的平坦处,住着几户人家,沟底有潺潺溪流沿村而过,为了出行方便,人们在村中建起一座小石桥,桥下的溪水可供人畜饮用,“桥儿沟”的名称就此流传下来。
不管哪个是真正的源头,从单桥一路到了这里,一种莫名的归属感油然而生。特别是滹沱河畔长大的人,会感到融入了一个庞大的精神体系,有一种就在这里的真实感受,并向外散发着能量。贴着滹沱河的5天行程,让一条河渐渐成为一体,从容地安顿好这种存在感。
查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幽州刺史部》,滹沱河是直接在青县入海的。那时,滹沱河叫虖池河,到献县后,分流为虖池河、虖池别河、虖池别水,后在青县汇合后入海。如今马厂减河便与这一段故道重合。从地图上看,子牙河沿用了虖池别水故道;我们往东寻访的只是虖池河故道。虖池河故道只留下河的蛛丝马迹,以桥、码头为多。像陈圈桥、河街桥、杨园桥、流海码头桥等。淮镇尚园子桥南,曾有赵家码头与砖厂,明永乐二年上元节奠基。砖厂烧好的砖,用黄纸包裹好,在赵家码头装船,沿滹沱河转道京杭大运河运至北京,建设北京城。北京城建好后,部分窑工并入上元子,逐渐形成尚园村;部分窑工在砖厂周围就地落户,形成前厂、后厂村;部分窑工居集为古里庄和郭庄。可想而知,当时码头与砖厂的规模。如今没有了踪迹,只能用仅剩的村庄名字,划出一个无形的轮廓。
大禹时代,献县以东,黄河时不时夺滹入海,黄河改道,滹沱河沿用了黄河故道。河是水的家,水不会分你家我家,能自由流动便好。水少了,水没有了,河的能量仍在,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单桥景区便是。
去过无数次单桥。上溯源头,下探入海口,当北排河、子牙河与京杭大运河立交而流时,我好像看到,一副镣铐牢牢地钉在滹沱河的脚踝上。滹沱河清晰地浮现出来,像一个人的命运,跌宕起伏。单桥似一面镜子,抑或一部大书中《不是尾声》的尾声,更像一个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躲藏在献县一隅。
这次溯源,正值滹沱河素颜季节。无论在车上、地上,见到的都是滹沱河的筋骨。物理的,精神的。溯源后,再次踏上单桥,或者曾经到过,抑或未到达的地方,都能抵达在滹沱河上见过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整条滹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