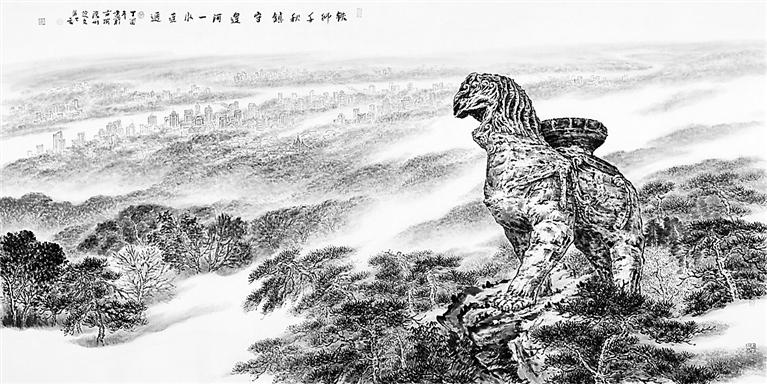奶奶的房子青砖青瓦,坐落在河道的石岸上,石岸下便是说不尽的运河。
住在这儿的老人说,那时运河边的农家,叫渔家,几乎家家有船,连同来往的商船,多得像水里的鱼。一旁的年轻人说,这都是神话吗?自打他们记事,满河筒子都是芦苇,死死活活的一线水。船没看到,倒是有人套着充气汽车内胎,用网兜捞鱼。还有就是那个钓鱼老头,多少年了?如果他是一棵树,恐怕早高过石岸,长到云彩中去了。
钓鱼的老头是爷爷,鱼是钓给奶奶吃的,奶奶吃鱼,只吃运河的鱼。奶奶是被运河的鱼水养大的,河水对她充满诱惑。奶奶没有离开过运河。她要守着爸妈,爸妈就睡在堤岸外的黄土下面,活着的时候,枕着水声入梦,现在更是,而且永远。何况还有一个男人让她生活在一种信念中。
男人是爷爷。爷爷对奶奶来说,是天赐也是恩赐!她永远记得那个最灿烂也最残酷的傍晚。即将沉没的落日,染红了天空和河水。远方沉雷隐隐,有经验的人判断,上游在下大雨。容不得往下说,高出水面半米多的浪头,翻滚而来,河水暴涨。水里有几个箱子漂浮过来,沿河住的人把漂浮的东西叫河利,凭本事,谁捞到是谁的。都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有时是胆大贪财的。他们低估了运河水,先是鼓起坟头一样的水包,越来越大,形成一堵惊涛骇浪的水墙。捞河利者被水墙砸进去。岸边的人惊呼,尖叫,顺着水流跑。被救的,救人的,开始像一溜拉链,后来散乱成开水锅里的饺子。奶奶的爸爸自小运河边玩水,玩成了一只水猫,他救上来两个人,体力消耗殆尽时,一条黑鱼,砸出一大片浪花,振臂,滑开一道水槽,向他抓去。
奶奶抱着气若游丝的爸爸,看着救爸爸的那个男人。他挣扎着试图站起来,原本一条硬邦邦的汉子,几次抬腿,都没成功,尔后,重重摔在地上。奶奶极柔极轻地擦着他的脸,使他睁开眼睛,看到俊美的奶奶和一碗鲜鱼汤。
老人没陪他们多久,留下了东厢房里的渔具就走了。东厢房墙面上,楔着木橛,挂着撒网、挂网、粘网、网罩、地笼、迷糊阵,旮旯还戳着渔叉。爷爷同样喜欢水,看到水就兴奋,从水的流动缓慢,鸟的起落方位,水草的深浅颜色,就知道哪儿有鱼没鱼,爷爷抢、摸、挂、撒、叉样样精通。但奶奶不让爷爷用这些渔具,奶奶只吃爷爷钓的鱼。
奶奶有私心。钓鱼不但陶冶情操,还能磨炼意志,锻炼耐力,达到一个“静”字。爷爷不用渔具,就不下水,那个悲惨的画面,碑文一样刻在她心上,奶奶认为不下水就没意外,还有爷爷在这钓鱼,不会淡出他的视线,这样踏实。爷爷是家,是港湾,是小船出入港湾拴缆绳的那块基石。爷爷不是每天都钓鱼,他和奶奶要依赖大地,保证五谷丰登的同时,让奶奶有鱼吃。钓鱼,也是钓意思。
生了爸爸和两个姑姑后,屋里多是快乐和鱼香。奶奶剩余的爱才是爷爷的。爷爷钓到小鱼,奶奶会说:“放回去吧,它从北京游到这里,才长这么大,等它游到杭州返回来,再下锅正好!”爸爸和姑姑们大笑,爷爷不笑,爷爷想变成一条鱼,游回家乡,但他不能,爷爷在救老姥爷的时候,也是自救。运河边上青色房子里,有他经营着的义务和责任。
奶奶爱吃鱼,先从爱做鱼兴起,运河多鲫鱼、鲤鱼、草鱼、鲶鱼、鳝鱼、鲢鱼,她来者不拒。可以烧吃,抠巴抠巴腮,摘除内脏,加点盐,用蓖麻叶子包好,放在灶膛余火里,少时,扒出,叶绿鱼鲜,仿若生时,但芳香四溢。奶奶还可以蒸、烤、炸、煮、熘,样样做到一丝不苟。
有串门的也来要:“婶,我想吃炖鲶鱼,再来一碗鱼咸肠,要有鱼肚脐的那种,另外,还有玉米饼没?”奶奶就笑着应答:“你个崽,我又不是开饭店的。”来人说:“问题是,饭店花钱买不到!”
爷爷喜欢吃酥鱼。奶奶给他做,这种鱼是用咸菜疙瘩和鲫鱼,要把鱼做到酥若无骨,咸菜疙瘩才有鱼味,比鱼好吃,爷爷原先也不喝酒,每晚奶奶逼他喝一杯,一杯也就二两,有时爷爷喝着掉泪,奶奶就抱着爷爷的头直到泪干。
这些吃的鱼都是爷爷钓来的,爷爷钓到姑姑们出嫁了,钓到爸妈去了城里,只余我守着老了的奶奶,和奶奶看着老了的爷爷钓鱼。
60年的垂钓,让爷爷不为世事所动。那天,突然激动,离开马扎,佝偻着身子急急忙忙往家赶,进东厢房,抄起渔叉。这一刻,奶奶心神大乱,嘱咐我别下石岸,跟着爷爷腹热心煎地来到水边。
进入奶奶眼帘的是一条大鱼,墨色背脊,门板一样长,两根长须轻摇慢拢,嘴一张一翕,吐着深奥的气泡。爷爷举起渔叉,奶奶抱着爷爷举着渔叉的胳膊,不说话,轻轻摇,轻轻摇,摇到脸上的泪水像凿开两道河。
爷爷的家乡在哪?爷爷不说,奶奶不问。也是那天,奶奶流着泪说:“要不你回吧?”爷爷看着深邃的天空,沉默很久说:“运河有鱼,我就不回!”奶奶心里一个热浪一个热浪的,奶奶说:“要是这样,运河有鱼,我就不走!”奶奶嘴里的“走”,让爷爷老泪横流。
运河在如烟的四季里衍生故事。除去雨季,河水漫过芦苇穗头。奶奶照样吃鱼,她身体的每个细胞已被鱼香浸透。爷爷照样钓鱼,爷爷选择钓鱼的角度,奶奶站在门口总能清晰看到,河道密匝匝的芦苇在风里摇曳,蓬起的芦花满天飞舞,水鸟岸边安居,或空中集翔,水淙淙,波纹粼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