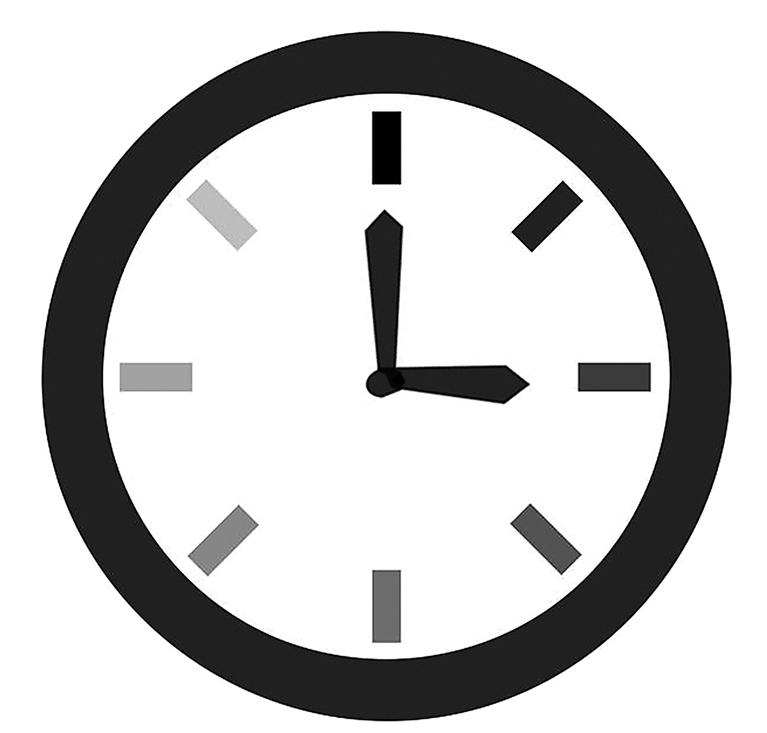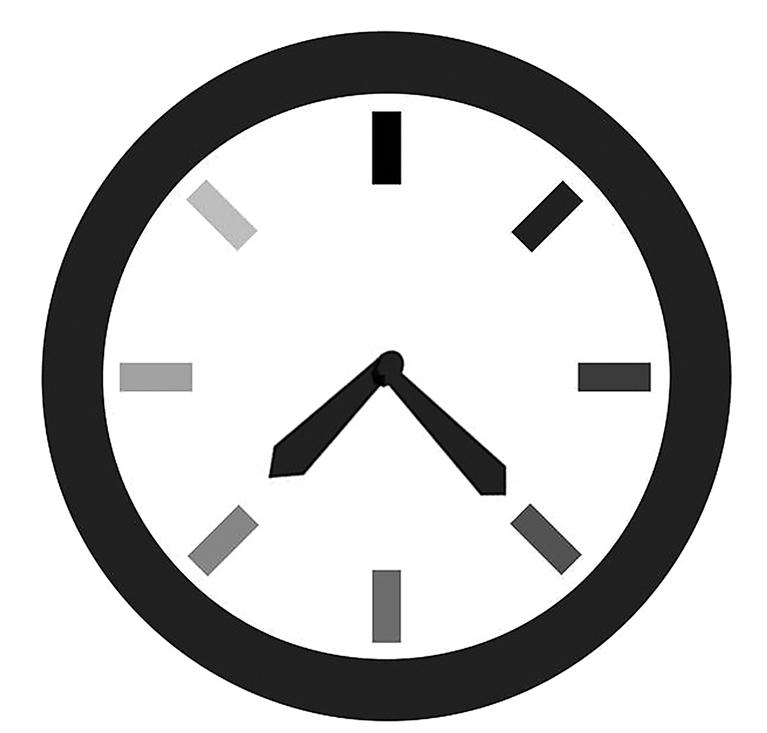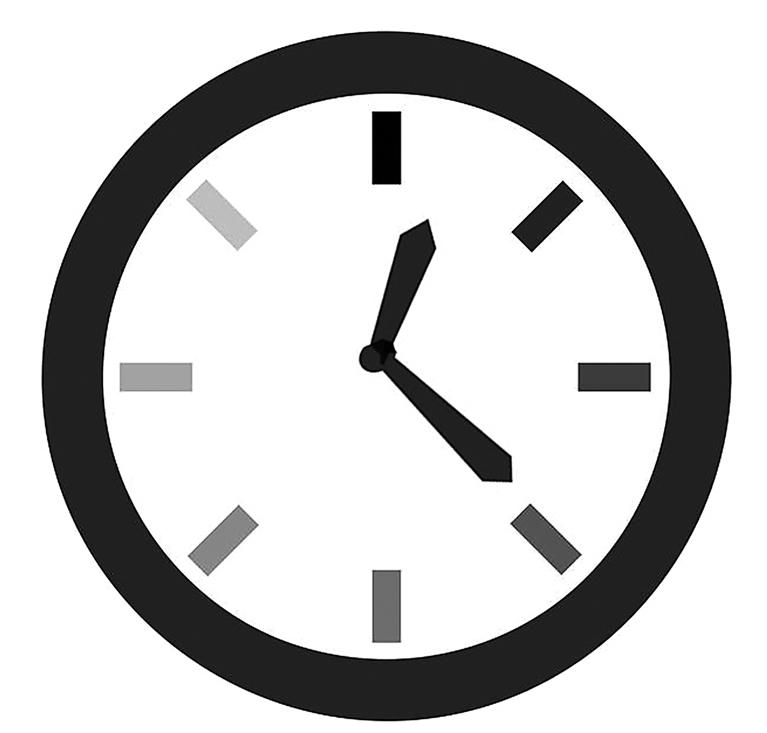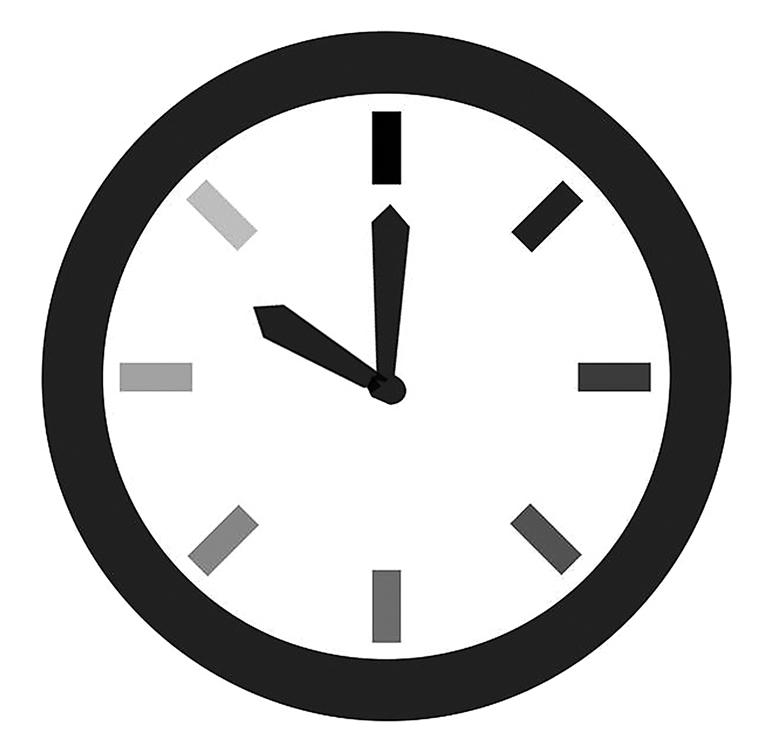赵松山和小麦打了一辈子交道。学生介绍他时,常用这样一句话:“穿几十元的背心,干上亿元的大事。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很多人都吃过他的粮。”
年少时,他从未想过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会成为自己的职业。他有过很多次机会走出这片麦田,但最终都留了下来。“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理解一粒好种子有多大的价值。”
赵松山书橱里的水杯整整齐齐摆了一溜,足有10多个。保温杯、磁化杯、紫砂杯、陶瓷杯……功能、材质各不相同,既有家人买来送他的,也有参加研讨会的纪念品,但无一例外,都没怎么用过,和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
他还是更喜欢用那个旧到已经变色、容量2000ml、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塑料杯,以致于这些年先后用坏了3个,也还是同样的选择。
他对水杯没有太多要求,“能装水就行,容量越大越好!”对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比起那些花里胡哨、玄而又玄,他更青睐实用和真实。
69岁的赵松山,退休前是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沧州试验站站长,也是沧州市农林科学院的研究员:“种子从来不玩儿虚的。优点再多,不能适应种植环境也是白搭!”
一条熟悉的路
走了许多年
离中科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还有一段距离,赵松山就已经坐不住了。这位和小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小麦育种专家,不停摩挲着那双磨砂纸般的手。这天,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试验数据需要确定。
5年前,赵松山从沧州农科院退了下来,但他和小麦育种的联系并没有终断。他受邀加入中科院遗传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振声课题组,继续开展抗旱耐盐碱小麦育种工作,并指导学生从事田间试验活动。
这条通往试验站的路,赵松山走了很多年。从沧州坐大巴到南皮县城,再坐4路公交车就能直达试验站。一路上,公交车从田地旁经过,阳光洒下来,和煦的光晕会给麦田覆上一片希望。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车还没停稳,赵松山就迫不及待地喊起来。
学生们闻声从院子里跑出来,眼睛笑成一道缝。
他们带来了赵松山想要的好消息。
“今晚能睡个好觉喽!”他开心得像个孩子,笑着从学生手中接过草帽,朝试验田走去。
穿几十元背心
干上亿元大事
“赵老师原本挺白的。”他的学生们说,长年在烈日下工作的缘故,他晒得像一匹斑马,衣服覆盖不到的地方比别处黑好几度。
赵松山的学生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在他们心中,眼前这个手提大水壶、头戴旧草帽、衣品跟农民没什么两样的老头儿,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他们常这样介绍他:“穿几十元的背心,干上亿元的大事。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很多人都吃过他的粮。”
这话并不夸张。
大多数育种人,穷尽一生,选育出一两个能通过国家级、省级审定的小麦品种就已相当不易,而赵松山却育成了14个,其中沧麦6001、沧麦6002和沧麦6005是沧州种植区域内的主推品种,沧麦6002和沧麦6005更是国家推荐的旱地小麦优良品种。早在12年前,他主持育成的品种就已累计种植8519.2万亩,增产25.79亿公斤,增加产值28.74亿元。
挨过饿的人
更懂种子的价值
年少时,赵松山从未想过,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会成为自己的职业。
他出生在运河区南陈屯镇大赵庄南队村,父母都是农民:“那时候,种子不行,地又盐碱,赶上好年份,小麦、玉米亩产也才200公斤左右。”
在赵松山的儿时记忆里,最揪心的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粮食短缺,人们都饿怕了。虽然国家有补助,但平均下来,我家每人每天仍只有二三两粮食。早晨和晚上只能喝稀粥,只有中午才有干粮吃,却也只是和着野菜、榆树叶的菜团子。”赵松山吃不饱,饿了靠水顶着,每年眼巴巴就盼着那几个节日和节气——春节、端午、中秋、立春和立夏。因为在前3个节日里,有年夜饭、粽子和月饼,而到了立春、立夏,按照传统,再不济也要想办法弄些面粉,烙张饼、下碗面。
几十年过去了,讲起那些往事,年近古稀的赵松山坐在椅子上,声音低沉,所有记忆归为一句话:“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理解一粒好种子有多大的价值。”
1971年,村民在当时沧州农科所驻村干部的带动下,种植了杂交高粱品种——晋杂5号。得益于其抗旱、抗病、耐碱、产量高的特点,头茬高粱亩产最高达450多公斤,比小麦、玉米高了1倍多。
看到优质种子带来的改变,同年秋天,村里又引进了40多个小麦新品种,并最终选种了其中两个。第二年,小麦亩产再创新高,村子一跃成为“沧州地区高产先进典型”。从那以后,赵松山再也没有了粮食不够吃的记忆,一颗学农的种子也在那一年种到了他心里。
40余年执着坚守
做麦田的守望者
1974年,赵松山被河北农大果树专业录取。
从庄稼汉成为本科大学生,所有人都为他庆贺,可赵松山却高兴不起来——灾年时,连哪一天能吃顿好饭都要精打细算,这样的日子,他不想再经历。他要研究小麦,培育更好的种子。
在大队书记的帮助下,他如愿来到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农学系。尽管从本科变成了专科,但赵松山满心欢喜——在学校图书馆,从报纸上看到山东小麦亩产550公斤的消息,他吃了一惊,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赵松山毕业后选择留校,从事春小麦育种栽培研究。1983年,他又回到沧州农科所小麦课题组工作。40多年的执着坚守,“等待”和“育种”成为陪伴他一生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
从一粒种子开始,抽出胚芽、长成幼苗、抽穗、开花、结实,这是自然的规律。因此,赵松山的工作周期也要以年为计。育种过程以人工杂交为主,通常,种子的性状表现要经过5到6个世代才趋于稳定,而一世代就是一年。此外,选育种子时,赵松山还要在以亩为单位的田地里,从天文数字的小麦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株。越是恶劣天气,他越要下田选种,麦收前的正午时刻,寒冬腊月的风雪天气,因为只在这时,育种材料才能表现出抗干热风和抗寒性的差异,才能真正确定品种的抗灾能力。再加上区域试验和审定,一个小麦品种,从培育到上市,即便顺利也要8到10年。
漫长的工作周期、艰苦的工作环境,很多育种工作者一生也培育不出一两个得意之作。原因有很多,研究方向的偏离,机遇的错失,或者只是缺少一些运气。毕竟,人生有几个8到10年?
赵松山也失败过,而且失败的次数远比成功的次数多得多。他有过很多次机会走出这片麦田,但最终都留了下来,原因还是那句话:“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理解一粒好种子有多大的价值。”
1996年,赵松山参加工作整20年,他培育的冀麦41成功通过审定,成为他的第二个“得意之作”。同年,冀麦41在他的老家大赵庄南队村大面积种植,收获时,亩产达到480公斤,比上一年高了90公斤。
那一天,他在麦田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夕阳西下,风吹麦浪,举目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