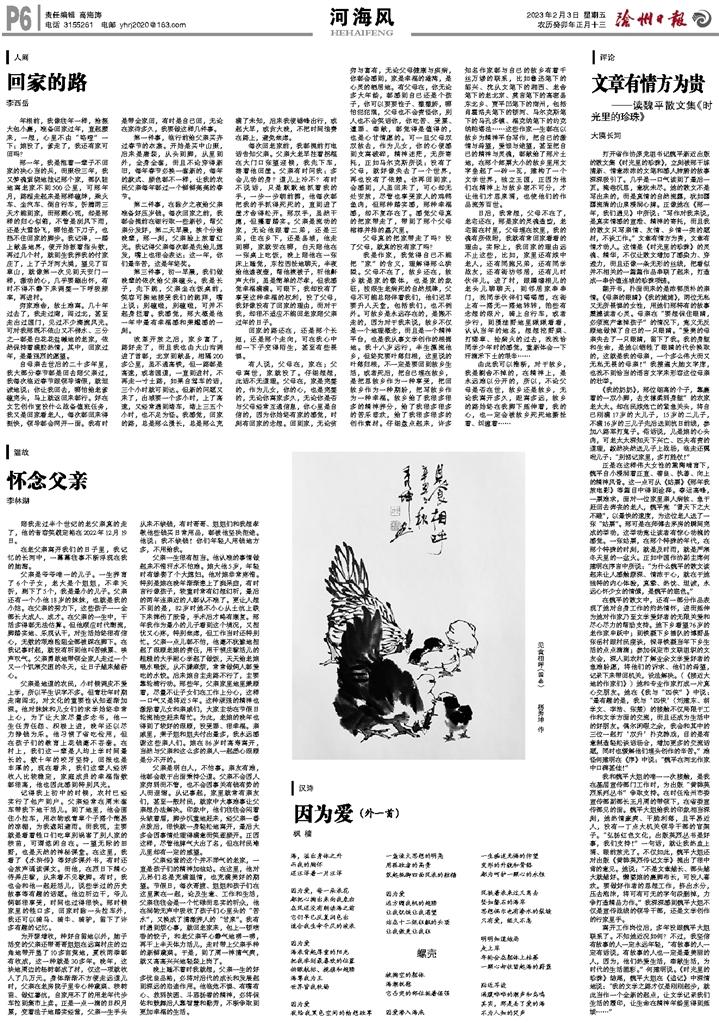年根前,我像往年一样,拾掇大包小裹,准备回家过年,直起腰来,一想,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娘没了,爹走了,我还有家可回吗?
那一年,我是抱着一辈子不回家的决心当的兵,而服役三年,我又梦魂萦绕地挂记那个家,部队驻地离老家不到500公里,可那年月,路程走起来是那样磕绊,乘火车、坐汽车、倒自行车,折腾两三天才能到家,而那颗心呢,却是那样的归心似箭,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哪怕是下刀子,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我记得,一踏上献县地界,便开始扳着指头数,再过几个村,就到生我养我的付家庄了,上了子牙河大堤,望见了百草山,就像第一次见到天安门一样,激动的心,几乎要蹦出怀,有时不得不静下来调整一下呼吸频率,再进村。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几十年过去了,我走过南,闯过北,甚至走出过国门,见过不少旖旎风光。可对我那既不依山又不傍水、三分之一都是白花花盐碱地的老家,依然保持着满腔热情,其中,回家过年,是最强烈的愿望。
自母亲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大部分春节都是回去陪父亲过,我每次临近春节跟领导请假,就坦诚地说:你让我回去,哪怕给老爹磕完头,马上就返回来都行。好在文艺创作室没什么战备值班任务,我又是回家看老人,每次都回来得挺快,领导都会网开一面。我有时是带全家回,有时是自己回,无论在家待多久,我要做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临行前给父亲买齐过春节的衣裳。开始是买中山服,后来是唐装,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身全套,而且不论穿得新旧,每年春节必换一套新的,每年的款式、颜色都不一样,让我的农民父亲每年都过一个鲜鲜亮亮的春节。
第二件事,在除夕之夜给父亲准备好压岁钱。每次回家之前,我都会提前在银行取一些新钞,帮父亲分发好,第二天早晨,挨个分给晚辈,那一刻,父亲脸上放着红光。我记得父亲每次都是先给儿媳发,嘴上也很会表达:这一年,你们最辛苦,这是年终奖。
第三件事,初一早晨,我们做晚辈的依次给父亲磕头。我是长子,先下跪,父亲坐在饭桌前,笑容可掬地接受我们的跪拜,嘴上说:别磕啦,别磕啦,可并不起身拦着。我感觉,那大概是他一年中最有幸福感和荣耀感的一刻。
改革开放之后,家乡富了,路好走了,而且我也由大山沟调进了首都,北京到献县,相隔200多公里,虽不通高铁,但一路都是高速,或者国道,一直到进村,不再走一寸土路,如果自驾车的话,三个小时就可到达。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出城要一个多小时,上了高速,又经常遇到堵车,堵上三五个小时,也不足为怪。我感觉,回家的路,总是那么漫长,总是那么充满了未知,后来我便错峰出行,或起大早,或贪大晚,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避免焦虑。
每次回老家前,我都提前打电话告知父亲。父亲大老早拄着拐棍在大门口张望迎候,我先下车,搀着他回屋。父亲有时问我:多会儿动的身?道儿上冷不?有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抓着我的手,一步一步朝前挪,他每次都把我的手抓得死死的,直到进了屋才舍得松开。那双手,虽然干瘪,但攥着踏实。父亲是流动的家,无论他跟着二弟,还是三弟,住在乡下,还是县城,他走到哪,家就安在哪,白天陪他在一张桌上吃饭,晚上陪他在一张床上睡觉,东拉西扯地聊天,半夜给他递夜壶,帮他掖被子,听他鼾声大作,虽是简单的尽孝,但我感觉幸福满满。可眼下,我却没有了享受这种幸福的权利,没了父母,我好像没有了回家的理由,而对于我,却很不适应不能回老家陪父亲过年的日子。
回家的路还在,还是那个长短,还是那个走向,可在我心中却一下子变得陌生,甚至有些畏惧。
有人说,父母在,家在;父母离世,家就没了。仔细想想,此话不无道理。父母在,家是完整的,作为儿女,你的心,也是完整的,无论你离家多久,无论你是否与父母经常互通信息,你心里是自信的,因为你始终有家的感觉,时刻有回家的念想。回到家,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父母健康与疾病,你都会感到,家是幸福的港湾,是心灵的栖居地。有父母在,你无论多大年龄,都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你可以耍耍性子、撒撒娇,哪怕犯犯混,父母也不会责怪你,别人也不会笑话你,你吃苦、受累、遭罪、奉献,都觉得是值得的,也是心甘情愿的。可一旦父母双双故去,作为儿女,你的心便感到支离破碎,精神迷茫,无所寄托,正如马尔克斯所说:没有了父母,就好像失去了一个世界,再也没有了依赖。你再回到家,会感到,人虽回来了,可心却无处安放,尽管也享受家人的鸡鸭鱼肉,但那种踏实感,那种幸福感,却不复存在了。感觉父母真的把家带走了,带到了那个父母棺椁并排的墓穴里。
父母真的把家带走了吗?没了父母,就真的没有家了吗?
我是作家,我觉得自己不能把“家”的含义,理解得那么狭隘。父母不在了,故乡还在,故乡就是家的载体,也是家的象征,按照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父母不可能总陪伴着我们,他们迟早要升入天堂,包括我们,也不例外。可故乡是永远存在的,是搬不走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精神平台,也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据地。我十八岁远行,半生漂流他乡,但终究要叶落归根,这里说的叶落归根,不一定是要回到故乡生活,或者死后,把自己埋在故乡,是把思故乡作为一种享受,把回故乡作为一种期盼,把写故乡作为一种幸福。故乡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精神养分,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苦乐悲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创作素材。仔细盘点起来,许多知名作家都与自己的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笔下的老北京、莫言笔下的高密县东北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包括肖霍洛夫笔下的顿河、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这些作家一生都在以故乡为精神平台写作,把自己的激情与希望,爱恨与绝望,甚至把自己的精神与灵魂,都献给了那片土地,在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里用文字垒起了一砖一瓦,建构了一个文学世界,独立王国,正因为他们在精神上与故乡密不可分,才让他们才思泉涌,也使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
日后,我常想,父母不在了,老宅还在,那是家的灵魂造型,老宅留在村里,父母埋在坟里,我的魂有所依附,我就有常回家看看的理由。实际上,我回家的理由远不止这些,比如,家里还有族中老人,还有同胞兄弟,还有同学战友,还有街坊邻居,还有儿时伙伴儿。进了村,跟蹲墙根儿的老头儿聊聊天,到邻居家串串门,找同学伙伴们喝喝酒,在街上有一搭无一搭地转转,拍些有念想的照片,骑上自行车,或者步行,到漫洼野地里瞅瞅看看,认认当年的地名,想想挖野菜、打猪草、捡柴火的过去,找找恰同学少年时的感觉,重新体会一下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由此我可以推断,对于故乡,我是割舍不掉的,在精神上,是永远难以分开的,所以,不论父母是否在世,故乡还是故乡,无论我离开多久,距离多远,故乡的路始终在我脚下延伸着,我的心,也一定会被故乡死死地撕扯着、纠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