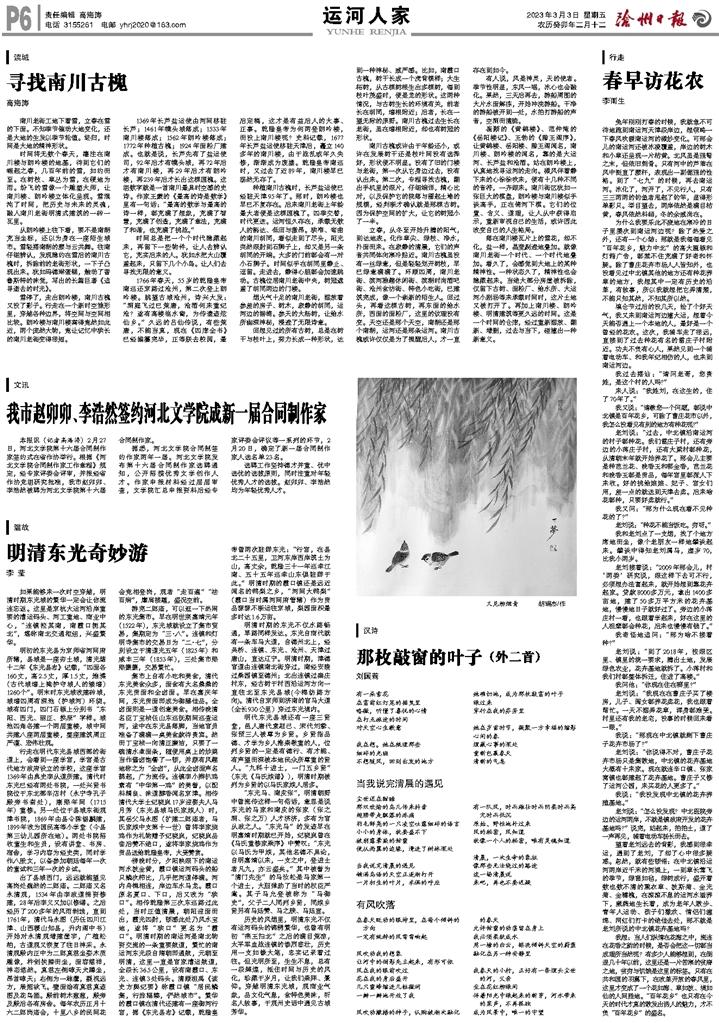兔年刚刚打春的时候,我就急不可待地跑到南运河天津段岸边,想领略一下春风吹暖南运河的微妙变化。可那会儿的南运河还被冰凌覆盖,岸边的树木和小草还呈现一片枯黄。北风虽是强弩之末,但依旧刺骨。只有河中的芦苇在风中挺直了腰杆,表现出一副倔强的性格。到了“七九”的时候,再去南运河。冰化了,河开了,不见行人,只有三三两两的钓鱼者甩起了钓竿,显得形单影只。举目望去,两岸依然是满目枯黄,春风依然料峭,冬的余威尚在。
为什么我要乐此不疲地在寒冷的日子里屡次到南运河边呢?除了热爱之外,还有一个心结:那就是我每每看见“百年花乡,魅力中北”的高大匾额和灯箱广告,都禁不住充满了好奇和怀疑。除了曹庄花卉市场人人皆知外,也没看见过中北镇其他的地方还有种花养草的地方,我想其中一定有历史的沿革,有故事,所以我就想把它弄清楚,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填仓节过后的没几天,捡了个好天气,我又来到南运河边撞大运,想着今天能否遇上一个本地的人,最好是一个曾经的花农。这次,我骑车走了很远,直接到了过去种花有名的雷庄子村附近。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见到一个骑着电动车、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也来到南运河边。
我过去搭讪:“请问老哥,您贵姓,是这个村的人吗?”
来人说:“我姓刘,在这生的,住了70年了。”
我又说:“请教您一个问题,都说中北镇是百年花乡,可除了曹庄花市以外,我怎么没看见有别的地方有种花呢?”
老刘说:“过去,中北镇沿南运河的村子都种花。我们雷庄子村,还有旁边的小蒋庄子村,还有大梁村都种花,从清朝末年就开始养花了。那会儿主要是种芭兰花、晚香玉和郁金香,芭兰花和晚香玉都是贡品,每年宫里都派人下来收。好的挑给娘娘、妃子、宫女们用,差一点的就送到天津去卖。后来啥花都种,只要好卖就行。”
我又问:“那为什么现在看不见种花的了?”
老刘说:“种花不能当饭吃。穷呀。”
我和老刘点了一支烟,找了个地方席地而坐,像个老朋友一样地攀谈起来。攀谈中得知老刘属马,虚岁70,比我小两岁。
老刘接着说:“2009年那会儿,村‘两委’研究说,照这样下去可不行,必须想办法富起来,就开始想到靠花卉起家。贷款8000多万元,拿出1400多亩地,建了50多万平方米的花卉基地,慢慢地日子就好过了。旁边的小蒋庄村一看,也跟着学起来,好在这里的人祖辈都会种花,后来也慢慢有钱了。”
我奇怪地追问:“那为啥不接着种?”
老刘说:“到了2018年,按照区里、镇里的统一要求,腾出土地,发展绿色农业,花卉基地就拆了。小蒋村和我们村都整体拆迁,住进了高楼。”
我问他:“你现在住在哪里?”
老刘说:“我现在在曹庄子买了楼房,儿子、闺女都养花卖花,我也跟着帮忙。一天不摆弄花草,浑身都难受。村里还有我的老宅,没事的时候回来看一眼。”
我说:“那现在中北镇就剩下曹庄子花卉市场了?”
老刘说:“你说得不对,曹庄子花卉市场只是集散地,中北镇的花卉基地大概有十来家。现在就连辛口镇、张家窝镇也都建起了花卉基地。曹庄子又修了运河公园,来买花的人更多了。”
我说:“我没发现中北镇的花卉养殖基地。”
老刘说:“怎么没发现?中北医院旁边的运河两岸,不就是镇政府开发的花卉基地吗?”说完,站起来,拍拍土,道了一声再见,骑着电动车扬长而去。
望着老刘远去的背影,我感到很幸运,遇到了老刘,了却了心中很多疑惑。忽然,就有些顿悟:在中北镇沿运河两岸近千米的河堤上,一到草长莺飞的季节,绿茵如毡,绿树成行,盛开着数也数不清的熏衣草、波斯菊、金光菊、金穗槐,在滚滚不息的运河水滋养下,葳蕤地生长着,成为老年人散步、青年人运动、孩子们撒欢、情侣们缠绵、网红们打卡的绝佳去处,那不就是老刘所说的中北镇花卉基地吗?
我想:当人们纵情在花海之中,流连在花香之韵的时候,是否会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呢?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在倒退几十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苦寒的贫瘠之地,贫穷与饥饿是这里的标签。只有在共和国的羽翼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这里才变成了一个花如海、草如波、境如仙的人间胜地。“百年花乡”也只有在今天的时代才真的散发出诱人的魅力,才不负“百年花乡”的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