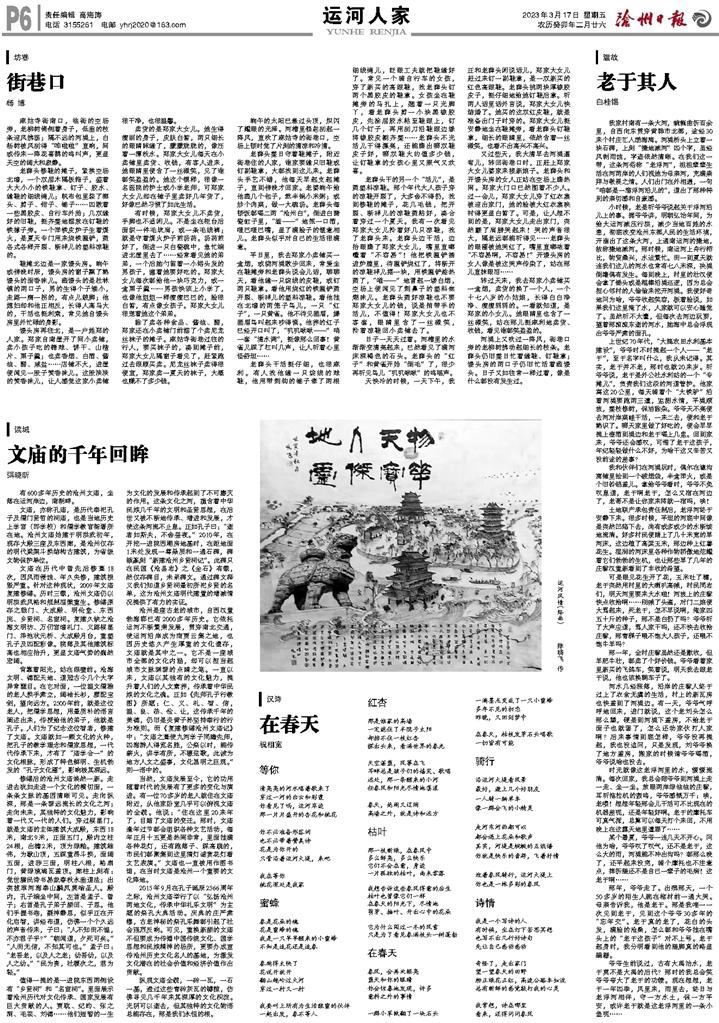麻姑寺街南口,临街的空场旁,老柳树倚侧着身子,低垂的枝条迎风拂荡;隔不远的河堤上,白杨树被风刮得“哗啦啦”直响,间或传来一阵花喜鹊的鸣叫声,更显天空的阔大和寂静。
老薛头修鞋的摊子,紧挨空场北墙,一个双层木隔板箱子,盛着大大小小的铁鞋掌、钉子、胶水、缝鞋的细线绳儿;帆布包里装了榔头、剪子、钳子、锥子……四散着一些黑胶皮、自行车外胎;几双缝好的旧鞋,挺齐整地摆放在钉鞋的铁撑子旁。一个洋铁皮炉子生着煤火,是夏天专门用来烧铁匾铲,烫各式各样开裂、断袢儿的塑料凉鞋的。
鞋摊北边是一家馒头房。晌午或傍晚时辰,馒头房的窗子飘了熟馒头的面香味儿。蒸馒头的是杜林镇的两口子,男的生得个子矮小,走路一瘸一拐的,有点儿跛脚;他媳妇却和他正相反,长得人高马大的,干活也挺利索,常见她自馒头房里外忙碌的身影。
馒头房再往北,是一户姓郑的人家。郑家自南屋开了间小卖铺,卖小孩子吃的糖球、饼干、山楂片、栗子羹;也卖香烟、白酒、酱油、醋、咸盐……店铺不大,进屋便闻见一股子焚香味儿。这股淡淡的焚香味儿,让人感觉这家小卖铺很干净,也很温馨。
卖货的是郑家大女儿。她生得瘦削的身子,皮肤白皙,两只细长的眼睛眯缝了,朦朦胧胧的,像汪着一潭秋水。郑家大女儿每天在小卖铺里卖货、收钱,有客人进来,她眼睛里便含了一丝微笑,见了谁都笑盈盈的。她这个模样,很像一名医院的护士或小学老师,可郑家大女儿却在铺子里卖好几年货了,好像已然习惯了如此生活。
有时候,郑家大女儿不卖货,手脚也不适闲儿。不是坐在柜台后面织一件毛坎肩,或一条毛线裤;就是守着煤火炉子煎汤药。汤药煎好了,倒进一只白瓷碗中,急忙端进北屋里去了……经常看见她的弟弟,一个后脑勺留着一小绺头发的男孩子,缠着她要好吃的。郑家大女儿每次都给他一块巧克力,或一盒栗子羹……男孩快该上小学了,也像他姐姐一样瘦瘦巴巴的,脸很白皙,有点像女孩子。郑家大女儿很宠着她这个弟弟。
除了卖各种食品、酱油、醋,郑家还在小卖铺门前摆了个卖尼龙丝袜子的摊子。麻姑寺街巷过往的行人,要买袜子的,凑到摊子前,郑家大女儿隔窗子看见了,赶紧跑过去照顾买卖。尼龙丝袜子卖得很便宜,郑家卖一夏天的袜子,大概也赚不了多少钱。
晌午的太阳已悬过头顶,炽闪了耀眼的光泽。河槽里倏忽刮起一阵风,直吹了麻姑寺的街巷口,空场上顿时觉了片刻的清凉和冷清。
老薛头整日守着鞋摊子,附近街巷住的人家,谁家要缝只旧鞋或钉副鞋掌,大都找到这儿来。老薛头手艺不错,他每天早起支起摊子,直到傍晚才回家。老婆晌午给他蒸几个包子,熬半锅小米粥;或炒个肉菜,做一大碗汤。老薛头每顿饭都喝二两“沧州白”,倒进白搪瓷缸子里,“滋——”地抿一口酒,咂巴咂巴嘴,显了满脸子的惬意相儿。老薛头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平日里,我去郑家小卖铺买一盒烟,或绕河堤散步回来,常爱坐在鞋摊旁和老薛头说会儿话,聊聊天,看他缝一只绽线的皮鞋,或钉两只鞋掌。看他用烧红的铁匾铲烫开裂、断袢儿的塑料凉鞋。看他挂在北墙的两笼子鸟儿,一只“红子”,一只黄雀。他不待见画眉,嫌画眉鸟叫起来吵得慌。他养的红子已经开口叫了,“叽叽啾啾——”哨一套“清水调”,挺像那么回事!黄雀儿踩了杠叫几声,让人听着心里怪舒坦……
老薛头干活挺仔细,也很麻利。有人找他缝一只绽线的球鞋,他用带刺钩的锥子牵了两根细线绳儿,眨眼工夫就把鞋缝好了。常见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穿了新买的高跟鞋,找老薛头钉两个黑胶皮的鞋掌。女孩坐在鞋摊旁的马扎上,翘着一只光脚丫,看老薛头剪一小块黑橡胶皮,先涂层胶水粘至鞋跟上,钉几个钉子,再用刮刀沿鞋跟边缘将橡胶皮割齐整……老薛头不光活儿干得漂亮,还能瞧出哪双鞋皮子好,哪双鞋大约值多少钱,让钉鞋掌的女孩心里又服气又欢喜。
老薛头干的另一个“活儿”,是烫塑料凉鞋。那个年代大人孩子穿的凉鞋开裂了,大多舍不得扔,找到修鞋的摊子,花几毛钱,把开裂、断袢儿的凉鞋烫粘好,凑合着穿过一个夏天。我有一次看见郑家大女儿拎着好几只凉鞋,找了老薛头来。老薛头边干活,边抬眼瞧了郑家大女儿,嘴里直嘟囔着“不容易”!他把铁匾铲插进炉膛里,待匾铲烧红了,将断开的凉鞋袢儿搭一块,用铁匾铲趁热烫了,“嗞——”地冒起一缕白烟,空场上便闻见了刺鼻子的塑料焦煳味儿。老薛头烫好凉鞋也不要郑家大女儿的钱,说是捎带手的活儿,不值得!郑家大女儿也不客套,眼睛里含了一丝微笑,拎着凉鞋回小卖铺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着。河槽里的水渐渐变清亮起来,已然看见了满河床深褐色的石头。老薛头的“红子”和黄雀开始“倒毛”了,很少再听见鸟儿“叽叽啾啾”的鸣唱声。
天快冷的时候,一天下午,我正和老薛头闲说话儿,郑家大女儿赶过来钉一副鞋掌,是一双新买的红色高跟鞋。老薛头挑两块厚橡胶皮子,挺仔细地给她钉鞋后掌。听两人话里话外言说,郑家大女儿快结婚了。她买的这双红皮鞋,就是准备出门子时穿的。郑家大女儿挺安静地坐在鞋摊旁,看老薛头钉鞋掌,细长的眼睛里,依然含着一丝微笑,也看不出高兴不高兴。
又过些天,我大清早去河堤遛弯儿,转回街巷口时,正赶上郑家大女儿婆家来接新娘子。老薛头和开馒头房的女人正站在空场上瞧热闹。郑家大门口已然围着不少人。过一会儿,郑家大女儿穿了红衣裳被迎出家门,她的脸被大红衣裳映衬得更显白皙了。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郑家大女儿走出家门,突然颤了肩膀哭起来!哭的声音很大,隔老远都能听得见……老薛头的眼圈被她哭红了,嘴里直嘟哝着“不容易啊,不容易!”开馒头房的女人像是被这哭声传染了,站在那儿直抹眼泪……
转过天来,我去郑家小卖铺买一盒烟,卖货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瘦瘦弱弱的。一看就知道,是郑家的小女儿。她眼睛里也含了一丝微笑,站在那儿挺麻利地卖货、收钱,看见谁都笑盈盈的。
河堤上又吹过一阵风,街巷口旁的老柳树拂动起细长的枝条。老薛头仍旧整日忙着缝鞋、钉鞋掌;馒头房的两口子仍旧忙活着蒸馒头。日子又如往常一样过着,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