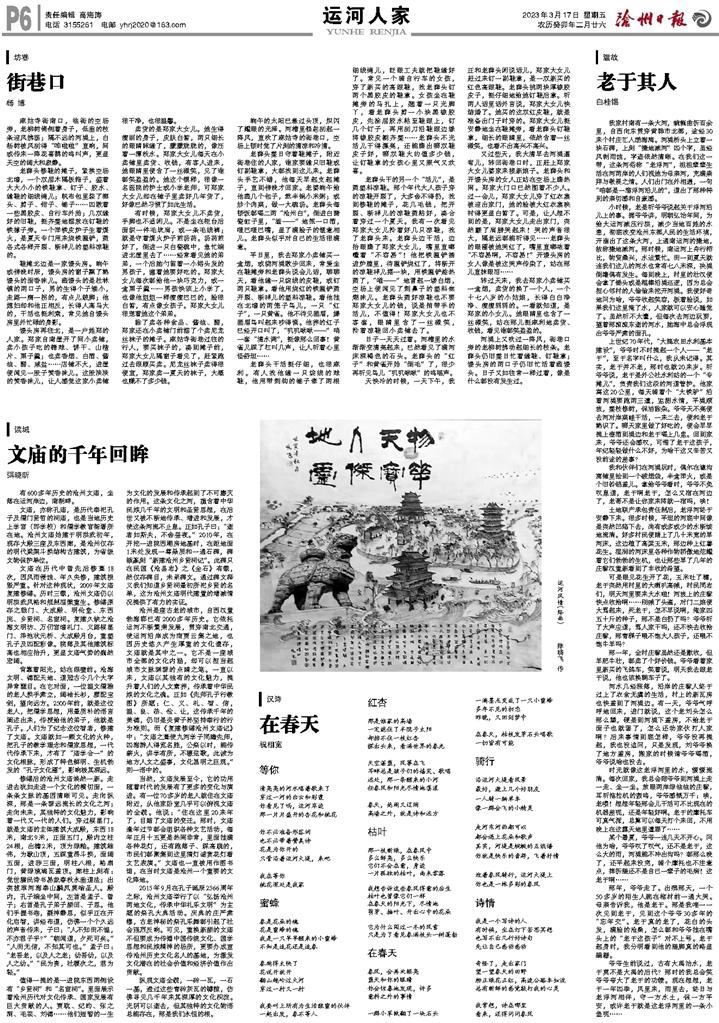我家村南有一条大河,蜿蜒曲折百余里,自西向东贯穿黄骅市北部,途经30来个村庄汇入渤海湾。河堤桥头上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捷地减河”四个字,虽经风剥雨蚀,字迹依然清晰。在我们这一带,这条河俗称“老浮河”,祖祖辈辈生活在河两岸的人们视她为母亲河,充满崇拜与敬畏之情。人们出门在外相遇,一句“咱都是一溜浮河沿儿的”,道出了那种特别的亲切感和自豪感。
小时候,老是听爷爷说起关于浮河沿儿上的事。据爷爷讲,明朝弘治年间,为给大运河减压行洪,减少当地百姓的水患,彻底改变沧州东部人民的生活环境,开凿出了这条大河,上通南运河的捷地,故称捷地减河。那时候,南运河上舟行栉比,物贸鼎兴,水运繁忙。而一到夏天就连我们这儿的河水也常有七八米深,决堤倒灌偶有发生。每到晚上,村里的壮汉便会拿了锄头或是棍棒沿堤巡逻,因为总会担心邻村的人偷偷来挖开河堤。我便好奇地问为啥,爷爷收起笑容,板着脸说,如果我们这里淹了水,人家就可以安心睡觉了。虽然听不太懂,但每次去河边玩耍,望着那滚滚东逝的河水,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爷爷严肃的面孔。
上世纪70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爷爷时不时提起一个人——“老于”,至于名字叫什么,我从未记得。其实,老于并不老,那时也就20来岁。听爷爷说,老于是外公社水利站的一个“专摊儿”,负责我们这段的河道管护。他家离这20公里,每天骑着个“大铁驴”沿着河堤要跑两三遭,监测水情,平堤顺坡,整枝修树,保洁除杂。爷爷天不亮便去河对岸菜畦干活,一来二去,便和老于熟识了。哪天家里做了好吃的,便会早早提上壶酒到堤边和老于喝上几盅。回到家来,爷爷还会感叹,可惜了老于这孩子,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为啥干这又辛苦又没前途的差事?
我和伙伴们在河堤玩时,偶尔在壕沟窝铺里捡到一个破烟袋,半盒洋火,或是个旧铃铛盖儿。拿给爷爷看时,爷爷不免叹息道,老于啊老于,怎么又宿在河边了,老哥不是让你家来将就一宿吗,唉!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老浮河终于安静下来。很多时候,平坦的河底中间像是突然凹陷下去,尚有或多或少的水断续地流淌。好多村民便瞄上了几十米宽的旱河床,这边植了高粱玉米,那边种上红薯花生。湿润的河床里各种作物骄傲地炫耀着它们勃勃的生机,也让那些旱了几年的庄稼汉重新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可是眼见花生开了花,玉米吐了穗,老于突然用村里的大喇叭高喊,村民同志们,明天河里要来大水啦!河坡上的庄稼快点收拾啊……刚喊了头遍,对门二娘便大骂起来,死老于,怎不早说啊,俺家四五十斤的种子,那不是白扔了吗?爷爷听了大声应道,骂人家干吗,还不快去收拾庄稼,那青稞子喂不饱大人孩子,还喂不饱牛羊吗?
那一年,全村庄稼虽然还是歉收,但羊肥牛壮,都卖了个好价钱。爷爷看着家里新买的飞鸽车,笑着说,明天我去跟老于说,他也该换辆车子了。
河水几经涨落,沿岸的庄稼人终于过上了衣食无虞的生活,村上的新瓦房也快盖到了河堤边。有一天,爷爷气呼呼地回来,进门就说,这个老刘头怎么那么犟,硬是到河堤下盖房,不给老于面子也就罢了,怎么还动家伙打人家啊?后来事情到底怎样,爷爷没再提起,我也没追问,只是发现,刘爷爷换了地方盖房,搬家的时候请爷爷喝酒,爷爷说啥也没去。
时光就像这老浮河里的水,缓缓流淌。每次回家,我总会陪爷爷到河堤上走一走、坐一坐。放眼两岸绿油油的庄稼,耳听拖拉机的轰鸣,爷爷感慨万千:唉,老喽!想想年轻那会儿干活可不比现在的机器差呢,还是年轻好啊。老于的摩托车可真气派,总算可以每天打个来回,不用晚上在这露天地里遭罪了……
某个暑夏,爷爷一连几天不开心。问他为啥,爷爷叹了叹气,还不是老于,这么大的雨,河堤能不冲出沟吗?都那么晚了,还平起来没完,骑个摩托也不注意点,摔折腿还不是自己一辈子的毛病!这老于啊……
那年,爷爷走了。出殡那天,一个50多岁的陌生人跪在棺材前一通大哭。母亲告诉我,他是老于。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老于,见到这个爷爷30多年的“忘年交”。老于真的老了,花白的头发,满脸的沧桑,怎么都和爷爷挂在嘴头上的“老于这孩子”对不上号。老于起身时,我分明看到他的腿脚真的略显蹒跚。
爷爷生前说过,古有大禹治水,老于莫不是大禹的后代?那时的我总会笑爷爷夸大了老于的功绩。现在想想,老于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终日与老浮河相伴,守一方水土,保一方平安,或许老于就是这老浮河里的一条小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