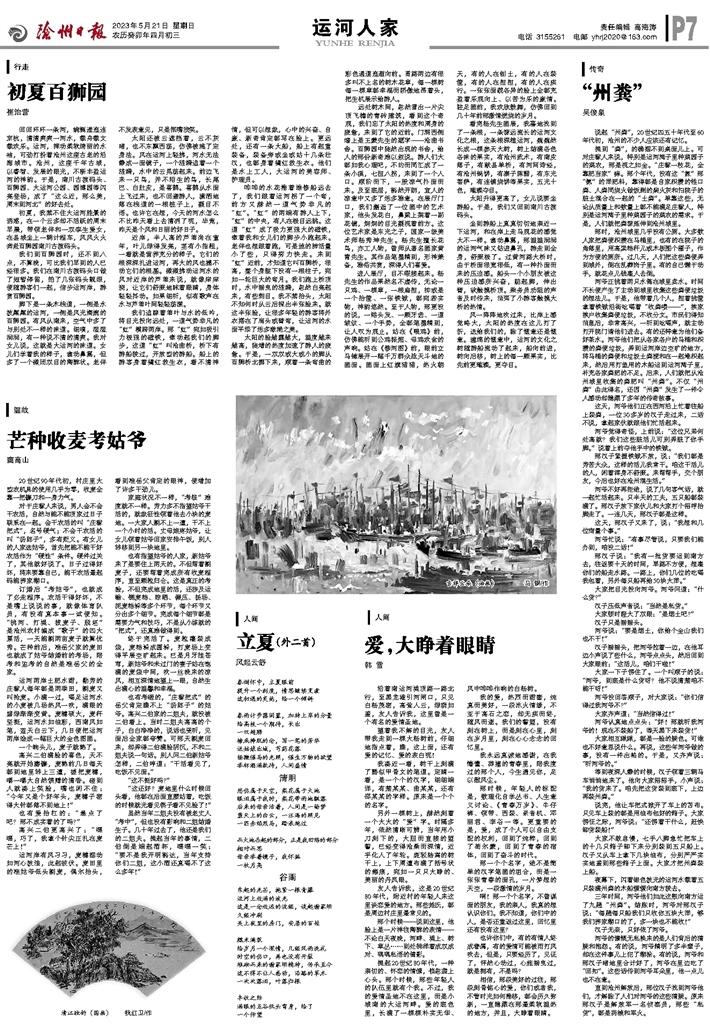说起“州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60年代初,沧州的不少人应该还有记忆。
提到“粪”,的确摆不到桌面儿上。可对庄稼人来说,特别是运河湾子里种菜园子的菜农,那是视之如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那个年代,没有这“氮”那“氨”的洋肥料,靠得都是自家积攒的牲口粪、人粪同烧火做饭剩的柴火灰和扫院子的脏土混合在一起的“土粪”。单靠这些,无论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庄稼人,特别是运河湾子里种菜园子的菜农的需求。于是,人们就把粪源延伸到沧州城里。
那时,沧州城里几乎没有公厕。大多数人家把粪便积攒在马桶里,也有的在院子的角落里,用高粱秸秆儿或木板围个圈子,作为方便的厕所。过几天,人们把这些粪便弄到城外,倒在乱葬岗子里。有的自己懒于动手,就花点儿钱雇人去倒。
河爷正挑着两只水筲在城里卖水。时间不长便产生了主动到城里收集这些粪便垃圾的想法儿。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担着挑筐拿着铁锨沿街吆喝着“收粪喽——”,挨家挨户收集粪便垃圾,不收分文。市民们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一听到吆喝声,就主动打开院门请他们进去。有的还特意为他们备好茶水。河爷他们把从各家各户的马桶和积攒的粪便垃圾,弄到运河岸边空旷的地方,将马桶的粪便和垃圾土粪搅和在一起堆积起来,然后用打鱼用的木船运到运河湾子里,补充各家粪肥的不足。后来,人们就把从沧州城里收集的粪肥叫“州粪”。不仅“州粪”由此得名,还因“州粪”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却隐藏了多年的传奇故事。
这天,河爷他们正在西河沿上忙着往船上装粪,一位30多岁的汉子走过来,二话不说,拿起家伙就跟他们忙活起来。
河爷觉得奇怪,上前说:“这位兄弟何处高就?我们这些脏活儿可别弄脏了你手脚。”说着上前夺他手中的铁锨。
那汉子紧握铁锨不放,说:“我们都是劳苦大众,这样的活儿我常干。咱这干活儿的人,闲着浑身不舒服。来帮帮手,交个朋友,今后也好在沧州混生活。”
河爷不好再拒绝,说了几句客气话,就一起忙活起来。只半天的工夫,五只船都装满了。那汉子放下家伙儿和大家打个招呼抬脚走了。一连几天,那汉子都是这样。
这天,那汉子又来了,说:“我想和几位商量个事。”
河爷忙说:“有事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办到,咱没二话!”
那汉子说:“我有一批货要运到南方去,往返要十天的时间,旱路不方便,想雇你们的船走水路。一路上,你们几位的吃喝我包着,另外每只船再给50块大洋。”
大家把目光投向河爷。河爷问道:“什么货?”
汉子压低声音说:“当然是私货。”
大家顿时瞪大了双眼:“是烟土吧?”
汉子只是摇摇头。
河爷说:“要是烟土,你给个金山我们也不干!”
汉子摇摇头,把河爷拉着一边,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河爷点点头,然后回到大家眼前:“这活儿,咱们干啦!”
大家一下子愣住了。一个叫顺子的说:“河爷,到底是什么货呀?他不说清楚咱不能干呀!”
河爷没回答顺子,对大家说:“你们信得过我河爷不?”
大家齐声道:“当然信得过!”
河爷认真地点点头:“好!那就听我河爷的!现在不装船了,等天黑下来装货!”
大家相互瞅瞅,都是一脸的疑色。可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再说,这些年河爷做的事,没有一件出格的。于是,又齐声说:“听河爷的。”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汉子领着三辆马车悄悄地来了。他向大家招招手,小声说:“我的货来了。咱先把这货装到底下,上边再装州粪。”
说完,他让车把式掀开了车上的苫布。只见车上装的都是用油布包好的箱子。大家愣怔之际,河爷说:“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卸货装船!”
大家不敢怠慢,七手八脚急忙把车上的十几只箱子卸下来分别装到五只船上。汉子又从车上拿下几块油布,分别严严实实地盖到那些箱子上面。大家才把州粪装上船。
夜幕下,闪着银色波光的运河水载着五只装满州粪的木船缓缓向南方驶去。
三年时间,河爷他们如此这般向南方运了九趟“州粪”。结账时,河爷对那汉子说:“每趟每只船我们只收你五块大洋,够我们养家糊口的了,多一块也不能收!”
汉子无奈,只好依了河爷。
河爷的慷慨无私换来的是人们背后的猜疑和抱怨。有的说,河爷精明了多半辈子,却在这件事儿上犯了糊涂。有的说,河爷和那汉子暗地里合计好了,河爷在里边吃了“回扣”。这些话传到河爷耳朵里,他一点儿也不在意。
直到沧州解放后,那位汉子找到河爷他们,才解除了人们对河爷的这些猜疑。原来那汉子是解放军一名侦察员,那些“私货”,都是药械和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