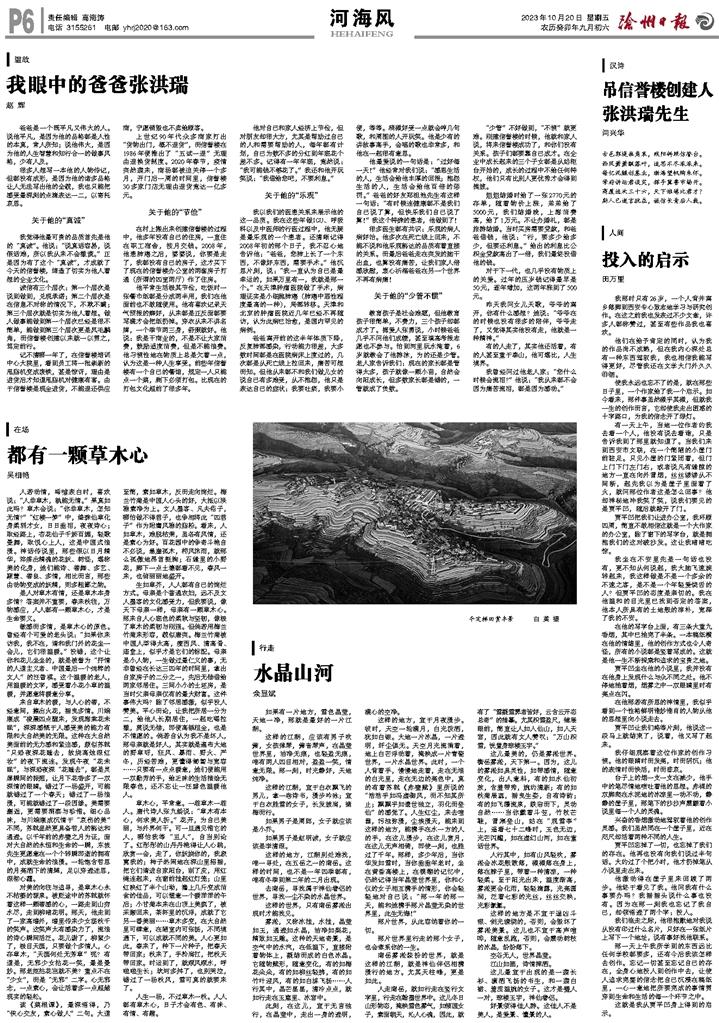人若动情,唏嘘表白时,喜欢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果真如此吗?草木会说:“你非草木,怎知无情?”“红楼一梦”中,绛珠仙草化身柔弱才女,日日垂泪,夜夜诗心;取经路上,杏花仙子千娇百媚,轻歌曼舞,取悦心上人,这是中国式浪漫。神话传说里,那些假以日月精华,淬炼出精魂的花妖、树怪,堪称美的化身,她们能诗、善舞、多艺、颖慧、善良、多情,相比而言,那些由动物变成的妖精,则多粗鄙之物。
是人对草木有情,还是草木本身多情?答案并不重要,春来秋往,万物感应,人人都有一颗草木心,才是生命要义。
敏感而多情,是草木心的原色。曾经有个可爱的老头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没错,这个让你和花儿坐坐的,就是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汪曾祺。这个温暖的老人,用温暖的文字,感受着小花小草的温暖,并愿意将暖意分享。
来自草木的暖,与人心的善,不经意间,擦出火花,摇曳多情。川端康成“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深深感慨于人感受美的能力有限和大自然美的无限。这种在大自然美面前的无力感和紧迫感,颇似苏轼“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夜下流连。发现午夜“花未眠”,与深恐夜深“花睡去”,都是灵犀瞬间的振翅,让月下花香多了一双深情的眼睛。错过了一场盛开,可能就错过了一个春天;错过了一场浪漫,可能就错过了一段因缘。美需要邂逅,更需要洞察与珍惜。细心品味,与川端康成沉情于“哀伤的美”不同,苏轼显然更具备哲人的豁达和通透。以千年前的赤壁之月为证,面对大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一瞬,东坡先生更愿意在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拥有中,成就生命的浪漫。一轮饱含哲思的月亮洒下的清辉,足以穿透迷思,照彻心霾。
对美的向往与追寻,是草木心永不枯萎的源泉。被贬途中的苏轼就怀着这样一颗善感的心,一路走到山穷水尽,走到柳暗花明。那天,他走到了一家高墙外,墙里传来少女荡秋千的笑声。这笑声太有感染力了,流浪的诗心瞬间活泛。花儿谢了,柳絮少了,极目天涯,只要做个多情人,心存草木,“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有道是,无邪少女拈花一笑,最是曼妙。那老妪拈花岂就不美?重点不在“少女”,而是“无邪”二字。心无邪念,一点素心,会让活着多一点超越现实的轻松。
读《菜根谭》,最深悟得,乃“侠心交友,素心做人”二句。大道至简,素如草木,反而走向绚烂。梅兰竹菊是中国人心头的好,大抵以淡雅素净为上。文人墨客、凡夫俗子,哪怕做不得君子,也争相将此“四君子”作为附庸风雅的脂粉。看来,人如草木,难脱枯荣,虽各有风情,还是素心为好。百花园中的争奇斗艳自不必说,悬崖孤木,栉风沐雨,就那么孤傲地昂首挺胸;石缝里的小野花,脚下一点土壤都看不见,春风一来,也俏丽丽地盛开。
生如草芥,人人都有自己的绚烂方式。母亲是个普通农妇,远不及文人墨客的文化感受力,但我要说,像天下母亲一样,母亲有一颗草木心。那来自人心底色的柔软与坚韧,像极了草木的柔韧与刚强。但倘若用梅兰竹菊来形容,貌似唐突。梅兰竹菊被中国人举得太高,瘦西风、清高骨、庙堂上,似乎才是它们的标配。母亲是小人物,一生做过最仁义的事,无非曾经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拿出自家房子的二分之一,先后无偿借给两家邻居住。三间小小的土坯房,是当时父亲母亲仅有的最大财富。这件事伟大吗?除了邻居感激,似乎没人赞美。平心而论,让我把所居一分为二,给他人长期居住,一起吃喝拉撒,莫说无偿,即便高额租金,也是不情愿的。倘若自认为我不是坏人,那母亲就是好人,其实就是遍布大地的野草呀,狂风、暴雨、野火、严冬,历经苦难,更懂得匍匐与宽容……只要有一点点暖意,她们便能用一双勤劳的手,给乏味的生活描绘无限春色,还不忘让一汪碧色温暖他人。
草木心,平常意。一茬草木一茬人。唐代诗人张九龄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花开,为自己美丽,与外界何干。可一旦遇见惜它的人,哪怕我等“丑人”,自当别论了。红彤彤的山丹丹艳得让人心跳,欣赏一会,走了,你妖娆你的,我寂寞我的;柿子热闹地在深山里招摇,把它们请进自家阳台,削了皮,用红绳连起来,在窗前挂起红灯笼;山里红映红了半个山坳,撸上几斤变成消食的佳品,可以惬意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小甘菊本来在山顶上美疯了,被采撷回来,茶杯里的沉浮,成就了它另一番美丽……草木多变,在大自然里可肆意,在陋室内可张扬,不同境遇下,可以成就不同的美。人心更如此,春来了,种下一片种子,把春天带回家;秋来了,手拎肩扛,把秋天带回家。时运到了,就顺风顺水,呼啦啦生长;坎坷多舛了,也别哭泣,错过了一场秋风,雪可真的就要来了。
人生一场,不过草木一秋。人人都有草木心,日子才会有色、有味、有情、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