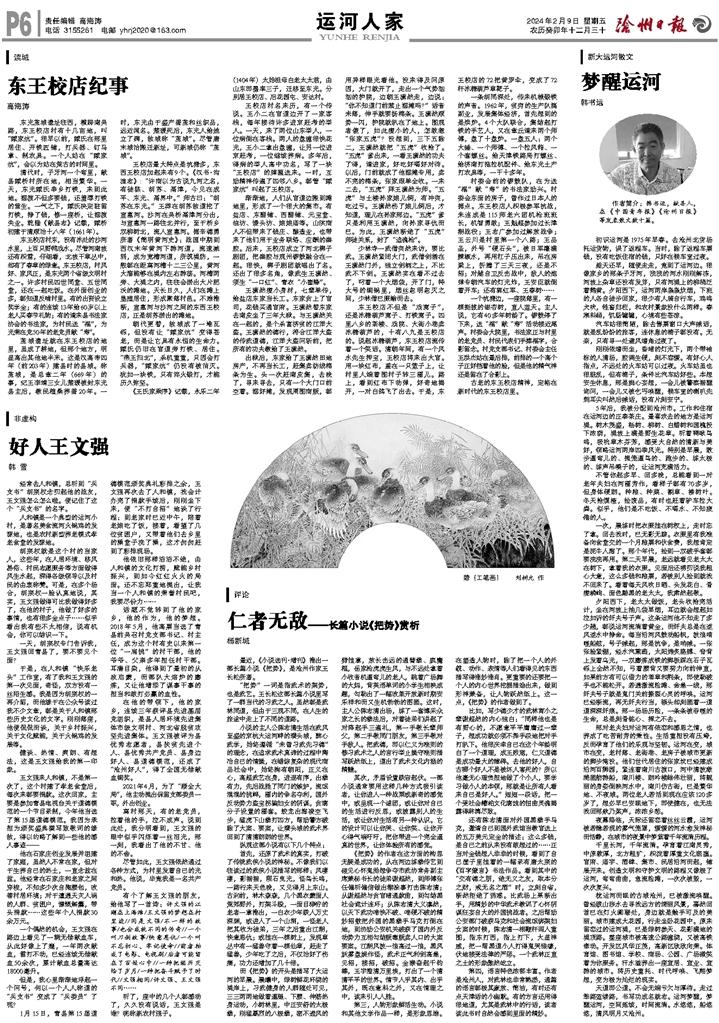作者简介:韩书运,献县人,在《中国青年报》《沧州日报》等发表散文数十篇。
初识运河是1975年早春。去沧州北货场托运货物,误了返程车。当时,除了返程车票钱,没有吃饭住宿的钱,只好在候车室过夜。
趁天还早,随便走走,竟到了运河边。很像家乡的那条子牙河,浅浅的河水刚刚解冻,河坡上杂草还没有发芽,只有河堤上的柳梢泛着鹅黄。夕阳西下,运河两岸袅袅炊烟,下班的人各自徒步回家,很少有人骑自行车,鸡鸣犬吠,牲畜归栏,和农村景象没什么两样。春寒料峭,饥肠辘辘,心境有些苍凉。
汽车站很简陋,除去售票窗口大声喊话,就是乱纷纷的旅客,连休息的椅子都没有。无奈,只有寻一处避风墙角过夜了。
刚刚依墙而坐,昏暗的灯光下,两个带袖标的人清场,腔调生硬,刻不容缓。有好心人指点,不远处的火车站可以过夜。火车站虽也很脏乱,但有椅子,条件比汽车站好些。本想安生休息,那是痴心妄想,一会儿被警察摇醒询问,一会儿又被乞丐唤醒,候车室的喇叭先刺耳尖叫然后喊话,没有片刻安宁。
5年后,我被分配到沧州市。工作和住宿在运河边的正泰茶庄。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运河堤。树木茂盛,杨树、柳树、白蜡树和国槐投下浓荫,堤坡上满是野生花草。听着啁啾鸟鸣,吸吮草木芬芳,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与美好,领略运河两岸四季风光。特别是早晨,散步遛弯儿的、提笼遛鸟的、跑步的、练太极的、练声吊嗓子的,让运河充满活力。
不管你起多早、回多晚,总能看到一对老年夫妇在河圈劳作,看样子都有70多岁,但身体硬朗。种粮、种菜、割草、搂树叶。冬天拾煤渣,捡废品,有时也赶着驴车拉大粪。似乎,他们是不吃饭、不喝水、不知疲倦的人。
一次,晨练时把衣服挂在树杈上,走时忘了拿。回去找时,已无影无踪。衣服里有我准备向食堂交的一个月粮票和伙食费,我想肯定是泥牛入海了。那个年代,捡到一双破手套都要洗洗再用。第二天早晨,老远就看见老太太在树下,拿着我的衣服。见面后还唠叨说我粗心大意,这么多钱和粮票,若被别人捡到就找不回来了。看着每天风吹日晒、头发花白、骨瘦嶙峋、面色黝黑的老太太,我肃然起敬。
夕阳西下,老太太做饭,老头收拾完活计,坐在河坡上抽几袋旱烟,耳边就会想起如泣如诉的纤夫号子声。这条运河他不知走了多少趟,都说运河流淌着黄金,而纤夫总是在逆风逆水中挣命。每当沿河风鼓动船帆,波浪啃噬船舷,号子喊起,那是抗争,是呐喊。一张张脸紧绷,经水汽熏蒸,太阳烤炙胳膊、脊背上发着乌光,一双磨炼成铁的脚板踩在石子瓦砾上全然不知,弓着腰背又要努力向前伸直,如果前方有可以借力的苇草和荆条,即使勒破手也不能松开。若遇激流险滩、命悬一线,那纤夫号子就是鬼门关前撕裂心灵的呼唤。运河已经断流,再无纤夫行当,额头却刻画着一道道深深纤痕。那一场场历险,一条条被吞噬的生命,总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那对老夫妇对运河有依恋和感恩之情,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秉性。生活重担没有压垮,反而孕育了他们的乐观与坚韧。运河在变,城市在变,老村落、老街巷、老房子被城市更新的脚步淹没。他们世代居住的张家坟已经建成沿河百狮园,紧连着南川古渡口,河中清波潋滟画舫游船,南川楼、朗吟楼雄伟壮丽,将靓丽的身姿倒映河水中,南川仿古街,已是繁华地、不夜城。两位老人若活到现在应该120多岁了,想必早已安眠地下,即使健在,也无法找回那欸乃桨声,浓浓乡愁。
夜幕降临,天际还留恋着丝丝云霞,运河被若隐若现的雾气笼罩,缓缓的河水愈发神秘而恬静,在城市的夜景中梦萦着千年流淌历程。
千里长河,千年流淌。孕育着江南灵秀,中原敦厚,北方粗犷,积淀着厚重文化底蕴。官府、庙宇、酒肆、集市、民居沿河而起,铺展开来。创造文明和守护文明的路程又像极了运河,弯弯曲曲,急流险滩,一次次被毁,一次次复兴。
枕运河而眠的古城沧州,已被激流唤醒。曾经跋山涉水去寻找远方的绮丽风景,蓦然回首已在灯火阑珊处,身边就是触手可及的美丽。城市建成大花园,行走坐卧花园中。原来留恋过的运河堤,已是绿树参天、花影满地的堤顶路。整座城市被高速公路缠绕,又被高铁牵动。开发区风华正茂,高新区欣欣向荣。体育馆、图书馆、学校、商场、公园、广场微笑着为你服务。汗水滋养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将历史重托、时代呼唤、飞翔梦想,变为极为灿烂的现实。
天道即公道。不会无端亏欠与厚待。走过筚路蓝缕路,书写功成名就志。运河梦醒,梦醒运河,空间延续,时间流淌。水悠悠,船悠悠,清风明月又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