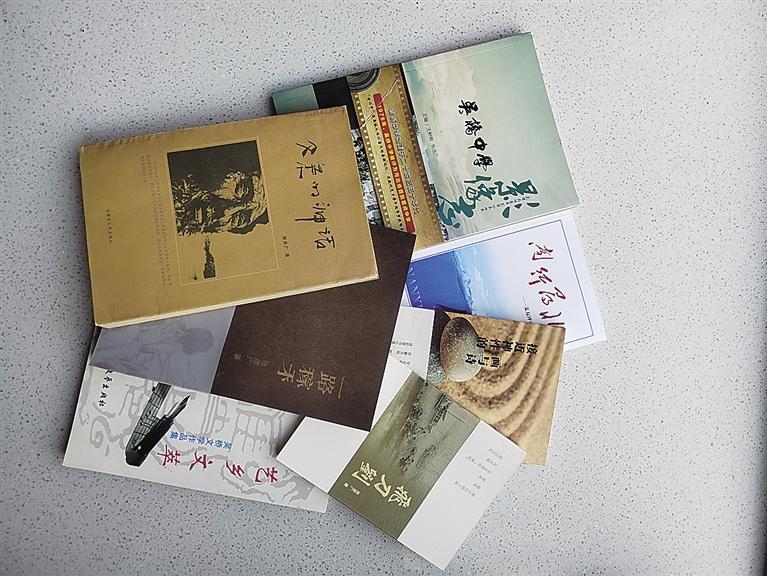从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张彦广走上文学道路已经37年了。目前,他正精心策划一本反映吴桥地方风物的图文著作。
身为一名散文创作者,张彦广以其深情的笔触关注农村、地域风情与人生百相,写出了《父亲的神话》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他的触角不局限于散文,还延伸至小说和剧本创作、文艺评论、报刊编辑、文化志愿活动等。
他质朴且富含哲理的散文植根于乡土并烙印在辽阔的土地上,对文学和本土文化的坚守使他在成长路上硕果累累。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倾听他对文学的思考,感受他对乡土文化的深深挚爱。
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是“减法”“除法”
记者:《飞刀刘》的灵感来源是什么?您是如何构思和塑造角色的?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彦广:与其说“飞刀刘”是一位杂技艺人,不如说他是一组杂技艺人的群像,是众多杂技英豪的复合体。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我听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一个耍飞叉的艺人胆子小,就怕见血,但后来却上了抗日前线。故事一下子击中了我,让我顿生创作灵感,很快“飞刀刘”就在我的心中成型了:我们的杂技艺人是顶着高粱花子的艺术家,他们热爱和平,追求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外敌入侵、铁蹄践踏的情况下,他们英武的血性又会瞬间爆发,实现从平民到英雄的迅速转型。
其实,在吴桥,这样的杂技艺人很多,比如吴桥杂技艺人张金奎,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红色杂技团——延安杂技团;当年抗美援朝志愿军文工团中有个杂技队,成员全部来自吴桥,而血染沙场的吴桥籍普通战士更是不胜枚举。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吴桥杂技艺人不仅有文化吉普赛人的一面,还有红色、爱国的一面,他们既能让自己吞钢球吃宝剑,也能让顽敌闻风丧胆。
这篇小说写得很顺利,发表得也顺利,先是在《百花园》发表,后又被《小小说选刊》转发,再后来又被收入两本小说集。前不久我上网时不经意发现,它还被收入为全国201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当代文学作品试题。
记者:《接近神性的画与诗》,收录了哪些作品?您对文艺评论写作有着怎样的见解?
张彦广:这些年丰富的经历,让我认识了许多作家、书画家等文艺工作者,一些人和作品走入了我的内心,化成了我的观感和洞见,变成了文字。还有一些作品,如给吴桥好人写的颁奖词,给杂技九月庙会写的吕祖祭文,给敬老饺子宴宣传册撰写的赋文,自己很珍视,也装进了这个“篮子”。《接近神性的画与诗》是给一位自闭症少年油画家画册写的序,语言诗性空灵,我对它情有独钟,干脆让它作了这本“杂论集”的题目。
当下文艺评论式微于文艺创作,而文艺批评更式微于文艺评论,我也未能免俗。我觉得如果你不敢“骂人”,那你“捧人”也要端正立场和认知,不逢不迎,不谄不媚,致中和,见真知,给读者架金桥,为世人当大媒。
记者:您为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张彦广:当走过了文字写作的语言技能关后,一座无形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那就是知见关。我个人常常徘徊于题材的认知和解读上,不敢轻易下笔。古人讲“文以载道”“敬惜字纸”,我们很多人对此都没生出敬畏心,文字信马由缰,看似高速高产,其实是不断巩固错误,制造精神垃圾。我的办法是,阅读时“非圣书,屏勿视”,处事时“能亲仁,无限好”,创作时“见未真,勿轻言”。其实从事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不是“加法”“乘法”,而是“减法”“除法”,淘尽黄沙始见金。
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
记者: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对文学产生兴趣的?这些年走过了怎样的文学之路?
张彦广:多少人走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天才和灵性,而我是因为困顿和挤压。第一篇铅字作品《拾粪》就是那个时候“挤压”出来的。
初中毕业后一年多劳累苦闷的打工生活,是一方磨刀石,逼我思索命运,催我宣泄情感,“豆腐块”“咸菜条”发表得越多,内心的不甘与躁动越强烈。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了命运意识和底层色彩,我靠文学自渡,而非渡人,泥菩萨过河而已。但是要感谢那个盛开文学梦的时代,感谢那些扶持后生的引路人,让我一步步跳出农门,一步步走进文学的伊甸园。
记者:您觉得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张彦广:1987年,我的文学作品已经变成了铅字,凭借这些作品,我竞聘上了乡广播站编播员。后来又凭更多的作品,我走进了县城,几易单位,不断成长。可以说,是文学在为我撑腰垫底、加油鼓劲。
市场经济大潮下,纯文学创作式微是事实,纸媒遭到冲击,一是因为传统媒体读者的锐减,二是因为很多创作者的信心渐渐丧失。靠文学能找工作、能转非转干的年代似乎远去了,其实是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人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知更加多元,读者要求作家既要是文化思想的方向标,又要是道德操守的定盘星,还要是心灵家园的守护神。所以我认为,当作家越来越难了。
记者: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早期代表作、并讲述它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吗?
张彦广:现在和文友们聚会,大家偶尔能聊到的我的早期作品,有《梦中的桐子姐》《破地》《父亲的神话》《飞刀刘》等一些篇章。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都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就是我的亲友或者我本人。我和这些作品因此也有了血缘,有了剪不断的精神脐带,甚至可以重组另外一个我。这个我,比你面前的我更真实、更立体、更有生命力。
写《父亲的神话》是缘于与一位老领导的交谈,他对我父亲这位“老河工”印象深刻,指出了我在对父亲认知上的深层次问题。那次交谈不仅匡正了我对父亲这一代人的认知理念,还提升了我对“三农”题材的审美水平。渐渐地,我的创作染上了土地的颜色,浸润上了乡愁的气韵。我曾经发誓,今生“要为农民歌唱”,也许我五音不全,声音很小,但我相信,低吟和呐喊都是最动情的歌唱。
要通过文学为地方文化赋形找魂
记者:您是如何将杂技、运河等地方文化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中的?
张彦广:吴桥杂技文化和运河文化博大精深,研究者和践行者前仆后继、代有才人。我也追求做这支队伍里的一分子。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创作里不能没有千年杂技梦,不能没有百里运河图,我要通过文学记住乡愁,为我们的地方文化赋形找魂。2018年,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盛大召开,与此同时,我在《沧州日报》文学副刊推出了一篇文旅散文《油葵花开》,影响不小。从那时起,我被誉为“新大运河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创作一发不可收。
记者:通过文学形式推广地方文化,您觉得有哪些优势和挑战?推出了哪些作品?
张彦广:吴桥是地域和人口小县,却是文化大县,这里是中国杂技的摇篮,是世界杂技的故里,千年大运河在这里穿境而过,滋润了这片土地,形成了优美奇绝的人文风情。在节假日,我经常挤进人流如潮的杂技大世界《找寻跨越千年的杂技精神》,从锣歌和春典里咂摸《舌根上的乡愁》。在清晨黄昏,我时常《走近三尊古槐》,追忆《山南水北的澜阳书院》,凭吊《建在月堤上的吴园》,为《寻找一根蒲棒》,在运河湾里《摆渡》,也时常《在运河右岸坐忘》,静等《帆峙水流艺乡梦》如期实现……
记者: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元素?对于初学者,您有什么创作建议?
张彦广:文学即人学。老家有句话叫“实在人长远”,那文学作品怎样才能“长远”呢?我想应该像大树一样,深扎生活的泥土,坚守脚下的位置,胸怀宽广如蓝天,心地慈悲泛爱众,即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记者:您如何看待创新与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
张彦广:自己才起步时,也走过“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弯路,直到一次有师友说我写东西“不较劲了”。我暗知,写了这么多年,我这才开悟,才真正上道儿。对于“道法自然”这句话来说,“创新”有时是个伪命题,日月轮回,人生行走,守常有定,反而日日即新。写作也如摄影,其记录功能最具终极审美意义。用文字为历史、为后人记住一些东西,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