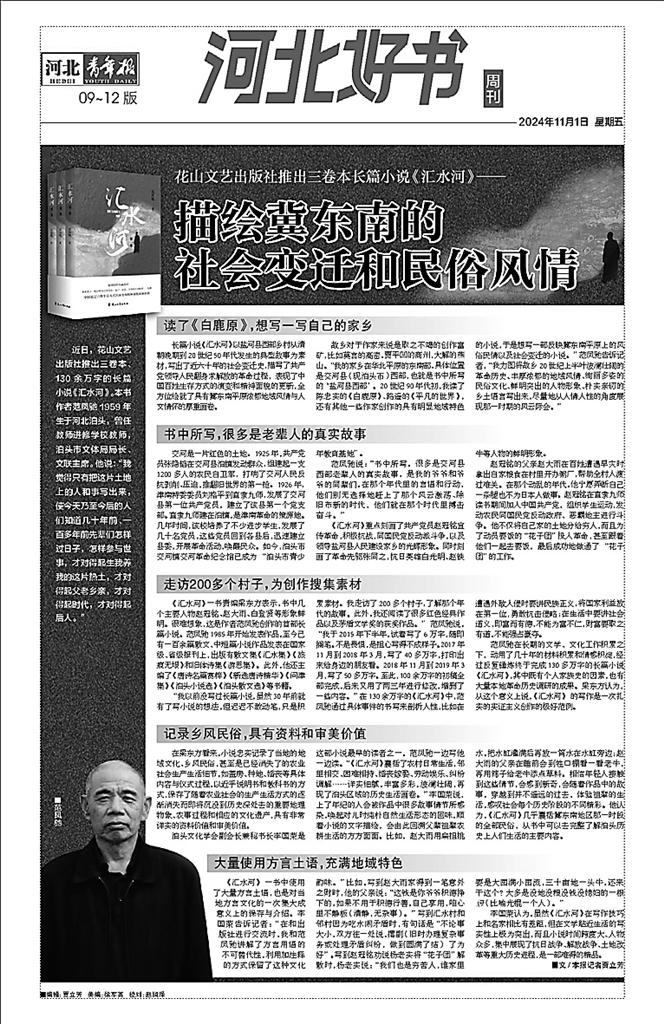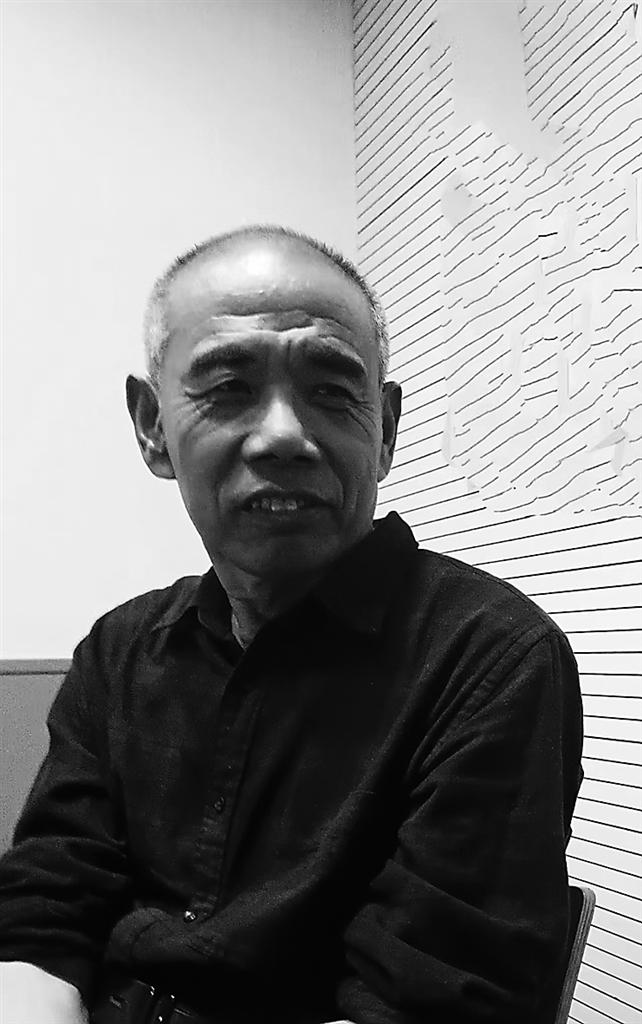作者简介:范凤驰,男,1958年12月生于河北泊头。大学文化,曾在泊头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曾任泊头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泊头市文化局长、泊头市文联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有100余篇散文、小说发表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出版有《唐诗名篇赏粹》《汉语修辞五十格》《新选唐诗精华》《问津集》《汇水集》《旅痕无垠》《游思集》《泊头小说选》《泊头散文选》《泊头诗歌选》《泊头诗词选》等多部图书。总计创作、编写了10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地方文史资料。
这一片土地,是黄河千万年造就的广袤平原。黄河曾几次流经这里,呼啸着、奔腾着流入大海。黄河不仅留下了深厚的黄土,也留下了激荡不息的众多河流,更留下了生动感人的古老传说和动人心魄的美好故事。黄河成就了这一方水土,也成就了这一方人的永久记忆。
这里有春天的野风,天昏地暗,黄土弥漫;这里有夏日的暴雨,浑水涌流,沟满壕平;这里有秋夜的明月,豆谷丰收,田野繁忙;这里有冬天的寒冷,肃杀孤寂,狂雪搅旋。在这块典型的黄河冲积而成的土地上,有一个建置并不很长的小县。它的名字并不响亮,既不叫这京那卫,也不叫这州那府,而是叫盐河县。人们往往去掉“县”字,称其为盐河地面。远远近近的人一提起盐河地面,大都有一种轻蔑的口气,暗含着这里的人老实、贫穷、生野。
盐河地面到底是个多大的地方,早些年人们没有丈量过,但都知道是一个长条形的区域,东西长南北窄,东部有一个靠运河的龙湾镇,是方圆百里都闻名的大镇;西部有一个京大路上的马岗驿,也是远近五县都来赶集上店的大镇;中间夹着一个盐河县城,像一根扁担担着两个大水筲。然而这一龙一马非斗即掐,总是合不拢,县官来了,两地的乡绅贤达都来拜见,抬自己压对方,龙湾镇的人得了势,就把马岗驿的人踩进泥里;马岗驿的人出了头,同样把龙湾镇的人扔到坑里。多数深知官场套路的县官来了,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地等着,把这根扁担放在地上,不挑在肩上,才能平安无事。即便偶尔放到肩上,也是按照当官的最高法则办事,掌握好平衡,两头儿都应承着,不叫扁担一头儿沉,压下去;一头儿轻,翘起来。平衡是当官最高的艺术,只有不偏不倚,才能稳当,像走钢丝一样。他们在离开盐河地面的时候,又说盐河地面的人好管,你给他一百个尊重,他还你一千个拥戴。只有少数官场套路不深的县官,来到盐河地面,一屁股坐在龙湾镇上,或者一屁股坐在马岗驿上,不出三个月,就像大小姐压跷跷板一样,上来下去地折腾,总是不能平身,地盘也就不稳,往往干不下三年,好的奉旨转任,不好的连官帽子都不翼而飞。也有几个县官,待了一段时间,被龙湾镇和马岗驿闹得无所适从,左右为难,觉得没有必要为个芝麻大的官帽子,作这么大的瘪子,干脆一走了之。所以,《盐河县志》上有两种说法,有的县官说盐河“民淳讼简,不相凌暴”“民性敦朴,务在农桑”。也有个别县官说“盐邑小县,号为难治”“龙湾镇五方之人杂处,人情浇漓”,这让盐河百姓既宽慰又脸红,真是情何以堪。
夹在这一镇一驿当中的盐河县城,真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团圆媳妇,两个婆婆都要伺候着。实际上,盐河县人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大事讲顺势,小事讲诀窍。凡事找到诀窍就好办,正像庖丁解牛,在骨肉的缝隙中下刀,事半功倍;又像庄稼人扬场,会扬的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片。来盐河县当官,就看你会当不会当了。
龙湾镇依靠着一条大运河,舟楫往来,商业红火,多年来形成了沿街叫卖、摆摊张罗、开店交易的商业文明。运河的岸边,一排排的大船小船停靠着,上面有的是皮货、粮食、布匹,还有的是官家专运的食盐、生铁和上好木材。龙湾镇的人每每笑脸迎接着那些上岸买东西的玩船人,一筐筐的鸭梨、小枣搬出去,一摞摞的光洋、铜子收过来,黄的金条、白的银锭也能常见,于是他们搭屋盖房,娶妻生子,身穿绫罗绸缎,手把玉石玛瑙。一天下来,紧盯着货物的眼睛累了,踅进屋里叫媳妇弄几个下酒菜,或者到街上拿回一个烧鸡,然后一口酒一口菜地快活起来。
马岗驿紧挨着一条南北大道,整日里人车穿梭,驿马奔驰,多少辈子生就了种地打粮、读书科考、忠孝传家的农耕文明。他们每天看到那些绿呢大轿抬着胸前贴着飞禽或走兽的官人,匆匆忙忙地行走。他们也看见一些穿长衫、戴毡帽的人担一个挑子,一头儿是书箱,一头儿是行李,满脸忧郁地往北走,进京赶考去。当然也有富裕人家的读书人牵个毛驴,驮着行李、书箱赶路。还有更富裕的人家套辆马车,有人驾车拉着读书人进京。过一段时间,有兴高采烈的人往南返了,那是考中进士、举人的,当然更多的人是满脸苦闷地往回走,他们落榜了。尽管这样,那些种地的人还是希望自己的祖坟上能够冒起一团一团的青烟来。途径自然是叫孩子们读书,龙种也好,跳蚤也好,反正要到场子上比划比划,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嘛。直到几次名落孙山,才认了头,断了念想。
久而久之,有人将龙湾镇和马岗驿的这种差异概括为秤杆文化和锄头文化,实际就是商业文明和农耕文明。两种文明中间隔着一道楚河汉界——鸿沟。
如果细细追究,龙湾镇和马岗驿只是近千年的辉煌,盐河地面真正的古老是在盐河县西部的汇水村,那里才是盐河县的老根呢。
单说在盐河县西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读书求仕、科考及第、光宗耀祖的人很是不少,而要是追溯盐河县西部读书的历史,掰着手指头掰扯过往的光环,更比这春天一片黄土、夏天一地黄泥精彩多了。整个盐河县西部没有文化的人能说上三天三夜,而稍微有点儿墨水的人则能说上十天半月,还不会重样儿。
他们说什么呢?首先要说到姜子牙这个老智星。直钩垂钓,离水一尺,还能钓上鱼来,这叫愿者上钩。有人说那是在渭水,跟你这黄土平原、穷乡僻壤有什么关联?且莫提那渭河,还是先说这盐河吧。商朝末年的时候,纣王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整日里酒池肉林,朝廷上下一派混乱,人民怨声载道。纣王还要大兴土木,建造宫室——鹿台,激起朝野上下怨声不绝,百姓造反的浪潮此起彼伏,西边的周人更是虎视眈眈,大有东进之势,商朝灭亡的征兆已很明显。大臣比干进宫劝说纣王,纣王说:“你的心黑了,我要把你的心肝挖出来烹炸,当饭吃。”纣王说得出就做得到,果真下令把比干杀了,还掏出鲜血淋淋的心肝,用油炸熟当了下酒菜。这一幕大臣箕子看得很清楚,出于对商王朝的忠诚,他又冒死进谏,结果纣王把箕子囚禁起来,择日砍头。箕子趁看守不备,逃了出来,远走朝鲜。大臣微子还想死谏,同乡贤人说:“不能再谏了,重复的事毫无意义,还是走吧,活下来还能给先人祭祀,不至于断了香火。这样虽然不能尽忠,也能尽孝。”微子听从了同乡的劝说,远远地离开了朝歌。到了山东的微山湖一带,躬耕田地,以打鱼为生,后来死在那里,于是那里的湖就叫微山湖,湖中的岛就叫微山岛。
姜子牙也是纣王的大臣,比干死了,箕子、微子走了,他怎么办呢?他想一旦商朝毁灭,自己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便学着微子的样子,在一个早上离开朝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东海棘津,以垂钓为乐。棘津这个地方离盐河不远,那时黄河还叫大河,正从盐河一带东流入海。姜子牙在大河岸边除了披一件蓑衣举竿钓鱼,还耕田种地,这一钓就是40年。一天,姜子牙正在大河岸边垂钓,不知不觉困神降临,他闭上眼睛,发出了鼾声,待到醒来时,一条大鲤鱼正在脚下翻身,再看那钓竿,早就不见了。姜子牙蹲下,双手拾起鱼来。只见大鲤鱼的嘴里叼着一片桑树叶子,再细看,叶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图案,是一个大大的圆圈升起来,分明是太阳升空的图像。姜子牙笑笑,觉得奇怪,但也没有在意,扔掉桑叶,拿起大鲤鱼就走。这时大鲤鱼说话了:“听说君子都步趋光明,怎么先生视而不见?难道先生有眼无珠,看不见太阳吗?”姜子牙听到大鲤鱼说话,心中又惊又喜,难道是自己施展才华的时机到了?他审视了一阵子大鲤鱼,说:“你要真是来点化我的,就请明言。”只见大鲤鱼甩动了一下尾巴,真诚地说:“你把我放回大河,咱们渭河上见。”姜子牙顿时醍醐灌顶,心里透亮透亮的。他把大鲤鱼放回河里,那颗怀才不遇的心又荡漾起来。姜子牙不顾已经72岁的高龄,背起鱼篓,穿好蓑衣,一路西行,到了渭河岸边。再后来他就遇到了周文王,智慧得到充分发挥,达到辉煌的顶点,成为千古“智星”。
盐河县西部的人认为,没有盐河县西部,姜子牙不会成为周文王的军师,盐河县西部才是姜子牙智慧的“发源地”,而汇水村正是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原先那里有一座钓鱼台,就是姜子牙钓鱼的地方,汇水村的古名就叫钓鱼台。
几百年后,盐河县西部出了一个尹吉甫。他是周幽王的大臣,曾经带着人攻打猃狁,又到盐河县西部作战,每战必胜。盐河县的人们说:“尹吉甫在盐河地面上的一次作战中,一个人杀死数十个敌人,战袍也被刺了十多个窟窿。”尹吉甫觉得盐河县西部的人善良厚道,就脱下战袍挂在树上,又把随身佩带的宝剑系在战袍上,才转身而去。回到朝廷,尹吉甫开始整理《诗经》,并亲手刊刻在牛的肩胛骨上,因此尹吉甫成为中国《诗经》第一人。其间他看到周幽王贪图享乐,荒废国事,就好言相劝。周幽王不听。尹吉甫觉得不能再在周幽王身边待下去了,把一部《诗经》送给盐河县西部的人民,只身回到故乡。后来,尹吉甫老死故里,盐河县人民将尹吉甫的战袍、宝剑和《诗经》一起埋了起来,并且堆起了高高的封土堆,这就是至今仍存在的尹吉甫墓。人们把尹吉甫看作是“仁”的化身。后来盐河县西部的人们每到寒食节,都去尹吉甫的墓地烧香叩拜,还要诵读《诗经》中一些篇章,以致后来毛亨、毛苌成了专注《诗经》的博士。
大河在盐河县西部又流淌了几百年,盐河县西部再次迎来一个圣人,严格说是官人和读书人的合体,名字叫刘德。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的第三个儿子。娶农家女为妻,在这里建造了日华宫,豪华气派。日华宫进门是长长的甬道,两边是四进的平房,磨砖对缝,青瓦起脊,每排房子的门楣上都标有文字,有收购室、库房、整理室、校对室、抄录室等。刘德有感于先秦古籍,特别是儒家经典被秦始皇焚掉不少,汉初又兴黄老之学,儒家典籍散失殆尽,便在国都以南三十里的黄河岸边盖起了百间房屋,招揽名儒大师聚集于此,整理辨析先秦古籍,然后刊刻。同时他还发出号召,让太行山以东的各地藏书者献书,辨别真伪后,高价收买真品,再重抄一份,让藏书人带回。刘德又指派一些地方文化名流,到各地求购书籍。他聘请的博士有毛苌、贯长卿等。他把几十位学人博士分为几组,辨别真伪,补缺校对,注释刊刻。刘德自己也常到日华宫来,和学士们一起读书、讨论、讲学,并同他们一块儿吃饭、睡觉,生活简朴,一时间深得山东文士的拥戴。他们整理的古籍能和都城长安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成为人人称道的佳话。刘德要全面恢复先秦的礼节,使社会文明发展。于是刘德的“礼”名长久地流传下来。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暴政与天灾逼得造反的农民和趁势的野心家蜂拥而起,不下几十伙儿百余万人。南阳粮商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公元22年与其兄刘[~公式~]加入了绿林军,打下宛城,拥戴以为容易控制的刘玄为更始帝,继承汉业。公元23年攻破长安,杀死王莽,定都洛阳。
更始帝的部队分为两派,一派是绿林军起义将领;一派是南阳豪族,以刘[~公式~]为首。绿林军嫉妒刘[~公式~]功高,撺掇更始帝杀死了刘[~公式~]。刘秀含恨忍痛,不敢服丧,假装无怨无恨,饮食谈笑如常。更始帝觉得愧疚,封刘秀为武信侯、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令其持节慰问河北州郡。
刘秀觉得这是脱离虎口、远走高飞的大好机会,立即整装启程,昼夜疾行。新野的邓禹曾对刘秀说:“更始帝没有能耐,不会成大事,你要广交天下英雄豪杰。做任何事,都要顺乎民心,争取了民众,才会成就大业。”刘秀在河北接见郡县长官及乡间士绅,解放囚徒,消除苛政,恢复汉官,受到了上层人士的欢迎。
公元23年,西汉时封于邯郸的赵缪王之子刘林将一个算命先生王朗当成了汉成帝之子刘子舆,立为天子,一时间势力遍及河北。他派使臣到各郡县去,悬赏杀死刘秀者封十万户侯。从此,势力孤单的刘秀开始了逃亡生涯,就是人们习惯说的“走国”。
公元24年正月,刘秀到达蓟州,蓟州的广阳王刘接起兵响应王朗。城中大乱,传说王朗的使臣到了,命令官员出城迎接。刘秀所带的一帮子人心神恐慌,急忙南逃,沿途不敢入城进镇,只能要饭充饥。刘秀在盐河一带,要饭讨水,艰难地等待着时机。盐河百姓看到刘秀的头上始终盘旋着一股紫气,觉得这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物,就极力地掩护他,拥戴他,给他行方便,帮他拉人马。很快,刘秀组织了一支团结凝力、所向无敌的队伍,他说:“等我有了天下,盐河百姓永不纳粮。”刘秀真是天子身份,该着称王掌管国家。在他称帝后,说话算数,整个东汉时期,盐河县的百姓一直不缴纳赋税。因此,盐河百姓又把刘秀看作是“信”的典范。
再到后来,窦建德从老家广川起兵,带领人马来到盐河县西部,走到两河相交的地方,发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想在这里建都立国。部将问他:“这里有什么好风水?”窦建德说:“你看这两河奔流,汇成大势,壮观呢,是昭示我们海纳百川,成就霸业呀,我们的队伍要扩大。”部将纷纷点头,表示赞成。窦建德又说:“昨天夜里我迟迟睡不着觉,等到睡着了很快做了一个梦,梦见五只大鸟,把各自的羽毛在河水里冲洗干净,然后冲着东方昂首挺立,齐声鸣叫,那声音极像皇宫里的乐曲,美妙动听。你们想这不是好兆头吗?”一个部将说:“你梦到的是什么鸟呢?”窦建德说:“是五彩缤纷的凤凰。”部将说:“大王说得在理,是好兆头,可是我们的地盘儿还是小了些,应当继续攻城略地,等再打下几十座城池,定鼎为好。现在天下未安,我们应当……”窦建德一听,也觉得自己目光短浅了些,一挥手说:“那就在这里建一个高台,既能让凤凰立于高处,还能引得更多的凤凰来。”于是窦建德命士兵在河边垒起了一个高台子,又修了一个亭子,以待凤凰来栖,然后率兵北上了。后人把这里的台子和亭子叫作五凤墩和五凤亭。
在隋末大乱的年代里,窦建德杀富济贫,治军严谨,深得百姓欢迎,很快占有大片疆土。他不忘前言,回到盐河县西部的两河交汇处,开国立都,名叫大夏,并以五凤作为年号,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因为这里是滹沱河和古高河的交汇处,城池在古高河的北边,河北为阳,山北为阴,便取名高阳城。后来,南边的王世充和李世民作战,向他求援。窦建德平生仗义,亲自带着十万人马南下援助王世充。不想马失前蹄,一败不兴。李世民没有杀死和他直接作战的王世充,倒把前来助战的窦建德砍了头,原因是窦建德勇敢聪明,深受百姓和部将欢迎,足以和李世民争霸天下,而王世充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不足成事。
盐河百姓把窦建德当作“义”的楷模,就在两河交汇处的南边为他建立祠堂,塑像纪念。几千年的时间里,盐河人,尤其是盐河县西部的人,都因为有这两条相交的河流而自豪。他们觉得正是这相交的河水给他们带来了福气,认为这里有着“仁义礼智信”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