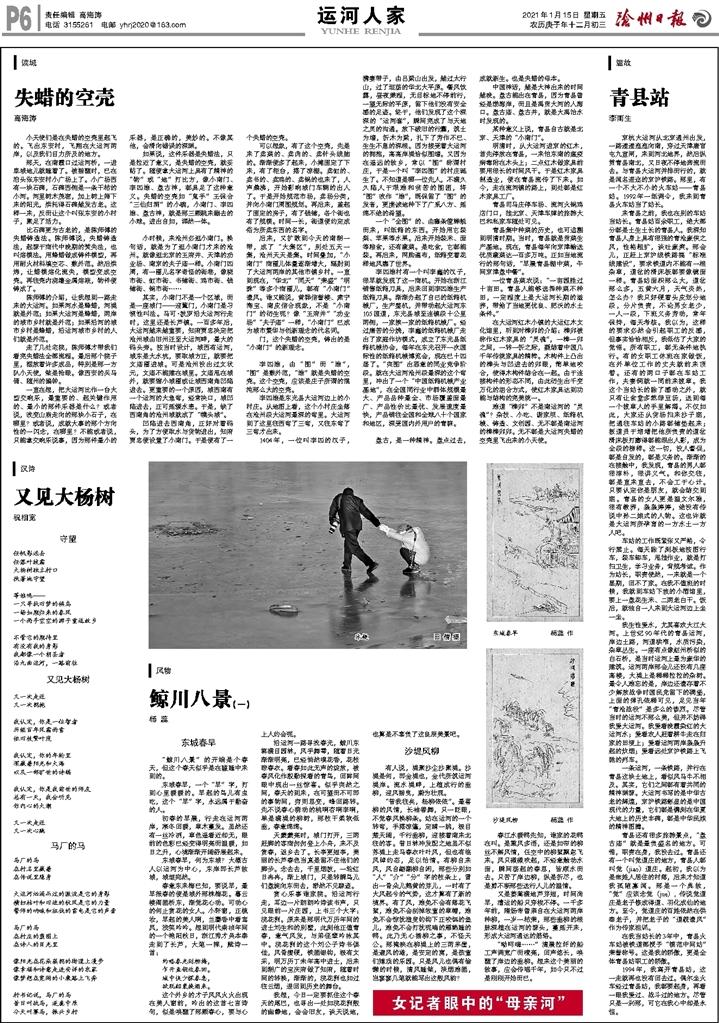京杭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一路逶逶迤迤向南,穿过天津唐官屯九宣闸,来到河北地界,然后纵贯青县南北,又日夜不停地奔流而去。与青县大运河并排而行的,就是闻名遐迩的京沪铁路。那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火车站——青县站。1992年一纸调令,我来到青县火车站当了站长。
来青县之前,我也在别的车站当站长。青县站百余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县人。我深知青县人身上具有很强的青沧豪侠之风,性格粗犷,谈吐豪爽。那会儿,正赶上京沪线铁路搞“标准线建设”,要求铁道内不能有一根杂草,道岔的滑床板都要像镜面一样。青县站面积那么大,道岔那么多,五黄六月,天气炎热,怎么办?我只好硬着头皮划分地段,分片负责,不论男女老少,一人一段,下班义务劳动,常年保持,每天考核。我以为,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引起职工的反感,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低估了大家的觉悟。所有职工,都无条件地执行。有的女职工休班在家做饭,在外单位工作的丈夫就前来顶替。还有的两口子都在车站工作,夫妻俩就一同前来拔草。我这个当站长的除了感动之外,就只有让食堂多熬绿豆汤,送到每一个拔草人的手里解渴。不仅如此,大家还从货场扫来沙子底,把通往车站的小路都铺垫起来;扳道员于培增把他所负责的道岔滑床板打磨得都能照出人影,成为全段的榜样。这一切,没人督促,都是自发的,都是义务的。渐渐的在接触中,我发现,青县的男人都很淳朴,很讲义气。和你交往,都是直来直去,不会工于心计。只要认定你是朋友,就会结交到底。青县的女人更是温文尔雅,很有教养,袅袅婷婷,绝没有传说中孙二娘式的人物。这也许就是大运河所孕育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吧。
车站的工作既紧张又严格,令行禁止。每天除了刻板地按图行车,装车卸车,甩挂作业,就是打扫卫生,学习业务,背规考试。作为站长,职责使然,一来就是一个星期,回不了家。在我不值班的时候,我就到车站下坡的小酒馆里,要上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饭后,就独自一人来到大运河边上坐一坐。
我生性爱水,尤其喜欢大江大河。上世纪90年代的青县运河,岸边土路,河道狭窄,水质污染,杂草丛生。一座有点像赵州桥似的白石桥,是当时运河上最为豪华的建筑。运河两岸那会儿还没有几座高楼,大堤上是稀稀拉拉的杂树。最令人难忘的是,岸边还遗存着不少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留下的碉堡,上面的弹孔依稀可见,足见当年“青沧战役”是多么的惨烈。尽管当时的运河不那么美,但并不妨碍我爱大运河。我爱看晚霞染红的大运河水;爱看农人赶着耕牛走在归家的田埂上;爱看运河两岸袅袅升起的炊烟;爱看远处京沪铁路上飞驰的列车。
一条运河,一条铁路,并行在青县这块土地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之间都有着共同的精神渊源。大运河书写的是中华古老的辉煌,京沪铁路彰显的是中国现代的力量,它们都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历史丰碑,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青县还有很多旅游景点,“盘古庙”就是最负盛名的地方。可惜,职责在身,我没去过。青县还有一个叫觉道庄的地方,青县人都叫觉(jiao)道庄。起初,我以为是焦姓人居住的村落,后来才知道我孤陋寡闻。那是一个典故,“觉”应该念觉(jue), 传说觉道庄是老子修成得道、羽化成仙的地方。至今,觉道庄的百姓依然在供奉老子,并把老子的“道貌遗风”作为传家祖训。
在我当站长的3年中,青县火车站被铁道部授予“模范中间站”荣誉称号。这是我的骄傲,更是全体青县站职工的骄傲。
1994年,我离开青县站,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偶尔坐火车经过青县站,我都要起身,再看一眼我爱过、战斗过的地方。尽管只是一刹那,可它在我心中却是永恒。